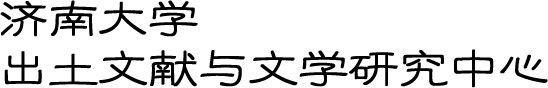前 言
本課題為战国楚簡帛文學文獻箋注,主要涉及九店楚簡、上博簡、清華簡、安大簡中的出土文学文献。
箋注由【題解】【釋文】【箋注】三部分構成,【題解】部分主要解釋該竹簡或帛書的主要內容,釋文部分呈现简之原貌。
體例標準如下:
1.釋文採用寬式隸定,不能隸定者則直接用原簡圖形植入。
2.每篇先列出竹簡釋文,在釋文中以①②③(上標)等形式,標示出需注釋的詞句。
3.對學者們有爭議的疑難字,依各學者文章發表之先後次序,羅列各家說法,再加按語【今按】提出本文所作之結論。注釋引用各批出土文献,對其原始整理者直接稱“整理者”,後續整理者统一按整理者人名(須加注年代),如:【李學勤1990】。
4.各家說法通常不在頁下注明出處,請以參考文獻的方式在文末體現,排列順序按著者姓名音序排序。
5.注釋中引用其他學者的表述,凡有明顯筆誤或者核對未精者,徑行改過,不一一指摘。
6.本專題採用符號大體依照簡帛文獻標注習慣。通假字、異體字隨文注明,加以()號;隸定有疑問的字,用(?)表示;訛字,用〈〉號標示;根據殘畫或文義可以補足的字,括注[ ](用细去粗,即改為宋體)號;殘泐或無法辨認的字,用☐號標示;殘泐字數不明或簡牘殘斷文意不足,用〼表示。
九店楚簡《告武夷》箋注
【題解】
1981年5月至1989年底,湖北江陵九店M56楚墓出土了146枚有字簡。該楚墓的下葬年代是戰國晩期早段,墓主身份爲“庶人”,竹簡內容以日書爲主體。《江陵九店東周墓》首次公佈了九店楚簡的圖版、釋文,《九店楚簡》對釋文進行了重新編連、釋讀,也載有圖版,是研究九店楚簡的通用版本。《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九店56號墓簡冊》《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五)·九店楚墓竹書》均著錄了紅外影像拍攝的圖版,吸收當時學界研究成果,釋文和注釋都有所修正、豐富;是九店楚簡研究成果的最新呈現。
《告武夷》是日書中的一個篇章,原無篇題,由整理者擬定。簡文內容爲祝禱辭,以“某”代替,是該類祝禱辭的通用的格式化文本。簡文既蘊含桑林神名、武夷避兵、祭禱招魂等傳説、民俗,且又爲韻文,文學色彩較濃。
【釋文】
《告武夷》①
【皋!②】敢告喪(桑)䌞(林)③之子武 (夷)④:“尔居
(夷)④:“尔居 (復)山之巸(基)⑤,不周⑥之埜(野),帝胃(謂)尔無事,命尔司兵死者⑦。含(今)日某
(復)山之巸(基)⑤,不周⑥之埜(野),帝胃(謂)尔無事,命尔司兵死者⑦。含(今)日某 (將)欲飤(食)⑧,某敢
(將)欲飤(食)⑧,某敢 (以)亓(其)妻上妻女(汝)⑨,【43】【
(以)亓(其)妻上妻女(汝)⑨,【43】【 (攝)】㡀(幣)⑩芳糧⑪
(攝)】㡀(幣)⑩芳糧⑪ (以)
(以) (量)
(量) (贖)⑫某於武
(贖)⑫某於武 (夷)
(夷) =(之所),君向(享)⑬,受某之
=(之所),君向(享)⑬,受某之 (攝)㡀(幣)芳糧,囟(使)⑭某⑮逨(來)
(攝)㡀(幣)芳糧,囟(使)⑭某⑮逨(來) (歸)⑯,飤(食)〖如〗故⑰。”【44】
(歸)⑯,飤(食)〖如〗故⑰。”【44】
【箋注】
①告武夷
【劉樂賢1996】擬題爲《祝語》。
【李零1997】擬題爲《禱武夷君祝辭》。
【整理者2000】擬題爲《告武夷》。
【今按】本篇共有兩枚簡,整理者編號爲43、44,兩簡簡首均缺一字。原簡無篇題,簡文內容爲祝禱辭,從整理者擬題作“告武夷”。
②皋
【李零1999】簡首缺文,可補“某”字。
【整理者2000】從文義看,缺文可能是巫祝字或“某”字。若是“某”字,此處的“某”與下文的“某”指代不同,前者似是指代巫祝,後者似是指代病人。
【周鳳五2001】據睡虎地秦簡《日書》甲乙種《夢》《出邦門》等祝禱文例,補釋爲“皋”。“上古祭祀祝禱之辭往往以‘皋!敢告’開端”,“皋”即“巫祝召請鬼神之前,爲引起注意發出的長聲號叫”。【陳偉2009,316頁】【黄儒宣2003,101—114頁】【陳偉、彭浩2021,44頁】結合從祝禱詞的文例,讚同周鳳五説。黃儒宣補充例證:周家嘉秦簡《已齲方》等病方“敢告”之前都是“皋”字。
【工藤元男2008】雖《日書》《士喪禮》均作“皋”,並不一定意味著九店簡此處必須復原爲“皋”字。
【今按】簡首字殘缺,整理者未釋。據出土文獻、傳世文獻中的祝禱辭體例,從周鳳五意見,補“皋”字。補釋“皋”字的意見,已爲較多學者接受,除前文所列陳偉、黃儒宣等學者意見,如【陳斯鵬2007】【工藤元男2008】【楊勇2020】【劉釗2024】所所録釋文均補釋“皋”,【楊勇2020】指出簡文中的“皋”是發語詞,此類禱辭,是以口説的方式進行。
③喪䌞
【李零1997】疑是“桑縢”。
【李家浩2003】第一字不可辨識未釋,第二字似是“䌞”。
【周鳳五2001】曹錦炎據《武夷山志·形勢》引《列仙傳》“籛鏗(彭祖)隱於此山,二子曰武曰夷”以論證“䌞”和“鏗”的古音相近,本簡缺字很可能爲“籛”字(或其通假字);當然,也存在“敢告【爾】䌞(鏗)之子武夷”的可能性。
【工藤元男2008】《列仙傳》並非劉向所撰,彭祖和武夷的關係上溯到先秦時期能否得到合理的解釋仍然存在疑問。實際上王叔岷的輯本等也暗示看不出彭祖(姓籛名鏗)和武夷的關係。
【陳魏後2014】“□䌞”所缺之字可能是“彭”,“彭䌞”即“彭籛”,“□䌞之子”即彭籛之子。彭祖是陸終之子,爲黃帝之後,與楚先祖季連是親兄弟,楚人祭祀彭祖之子“武夷”乃先祖崇拜。
【白於藍2003】從殘存字形看,第一字李零釋爲“桑”可能是對的,第二字應從李家浩釋爲“䌞”,“桑䌞”,待考。又白於藍十多年前曾在《讀九店簡筆記》一文提出“桑林”的釋讀意見與論證思路,惜缺少關健證據,這則筆記未發表,也未收入《九店楚簡整理》結項報告和《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詳見【程少軒2018】附記,【陳偉、彭浩2021,44頁】注也提及曾疑“桑䌞”應讀爲“桑林”。
【程少軒2018】“□䌞”是武夷之父的名字。第一字李零釋爲“桑”,第二字李家浩認爲似是“䌞”,白於藍綜合兩者説法釋爲“桑䌞”都是正確的。更嚴格地説,第一字釋爲“桑”的分化字“喪”更爲準確。武夷之父“喪䌞”應該就是文獻常見的鬼神“桑林”。傳世文獻所見“桑林”有三層含義:一是用爲地名,爲商湯禱旱之地,後來成爲宋國社稷所在地;二是用作樂舞名;三是用作鬼神名。這三重含義應該是有關聯的。正因爲桑林是殷人的聖地,殷商後裔宋才將專有的祭祀樂舞命名爲《桑林》,亦由此衍生出同名的鬼神。“喪、䌞”與“桑、林”除了音韻相通毫無障礙,還因爲“桑林”和“武夷”在文獻中常同時出現,是關係密切的一對神靈。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太一祝圖》右邊神靈題作“武弟子,百刃毋敢起,獨行莫〼”,左邊神靈殘存題記文字爲:“桑林,百兵毋童(動)〼禁。”由過題記可知,“武弟(夷)子”“桑林”兩個神靈皆與避兵有關,職能相似。在《太一祝圖》中,兩者並排站立,姿勢相同,容貌髮飾也幾乎一樣,繪圖者顯然在刻意表現他們之間的密切關係。東漢之後的解注類文獻中,有神靈“倉林君”“蒼林君”與“武夷君、武夷王”的配對,顯系有意爲之。“蒼、桑”古音極近,可以通假,“倉林、蒼林”和“桑林”是同一個神。“桑林”和“武夷”頻繁地成對出現,要麼共同避兵,要麼共同治鬼,職能高度一致。在戰國楚簡中作爲父子的“桑林”和“武夷”,後世被附會成職能類似的神靈,符合民間信仰流變的一般規律。
【陳偉、彭浩2021】從殘存字形看,第一字應從李零釋爲“桑”,第二字應從李家浩釋爲“䌞”。
【劉釗2024】九店簡《告武夷》揭示了武夷神的執掌是“司兵死者”,即負責管理戰死之人。從九店簡《告武夷》“敢告喪(桑)䌞(林)之子武夷”,可知“喪(桑)林”与“武夷”是父子关系,这是以往不知道的新知。正因爲“喪(桑)林”與“武夷”是父子關係,所以在鎮墓文和道書中兩者並提,在帛畫中兩者也是並排站在一起。宋白玉蟾著《修真十書武夷集》載《武夷重建止止庵記》説:“武夷之爲山,考古秦人《列仙傳》,蓋篯鏗於此煉丹焉。篯鏗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後謂之彭祖,年及七百七十七歲而亡。生平惟隱武夷山,茹芝飲瀑,能乘風禦氣,騰身踴空,豈非仙也耶?鏗有子二人,其一曰篯武,其次曰篯夷,因此遂名武夷山。”疑“喪(桑)林”“篯鏗”兩名應是同一個名字在不同時代的變異,而“彭祖”則是從另一個角度起的異名。
【今按】程少軒“喪”、李家浩“䌞”的釋讀,程少軒、劉釗等“喪䌞”訓讀爲“桑林”的意見均可行。文獻中有“桑林”神的記載,《淮南子·説林》“桑林生臂手”高誘注:“桑林,神名。”楊伯峻、徐提(1985)指出《左傳》中“桑林”總有“宋社名;又樂舞名;又鬼神名”三義。文獻中亦有桑林爲祟的記載,杜鋒(2019)已有論述。文獻中桑林、武夷兩神並不罕見,不過誠如劉釗所言,九店簡提供了“喪(桑)林”与“武夷”是父子关系的新知。
④武
【李家浩1993】司兵死者的“武夷”是馬王堆帛書避兵圖的“武弟子”。
【饒宗頤1997】武夷君乃天帝命之司兵死者。
【整理者2000】《漢書·封禪書》記武帝時人上書所説的神祇有“武夷君”,湖北武昌出土的齊永明三年劉顗買地券所記神祇有“武夷王”,馬王堆漢墓帛書《太一避兵圖》所繪神祇有“武弟子”。“夷”“弟”二字古音相近,可以通用。疑簡文“武 ”與此“武夷君”“武夷王”“武弟子”是同一個神。
”與此“武夷君”“武夷王”“武弟子”是同一個神。
【工藤元男2008】李家浩將帛畫的“武弟子”讀爲“武夷子”是可取的,武夷爲先素至秦漢時期的“避兵之神”這一點是顯然的。
【劉釗2024】馬王堆漢墓帛畫《太一將行圖》有“武弟(夷)子,百刃毋敢起,独行莫”,李家浩讀“弟”爲“夷”,説“子”爲尊稱,指出“武夷”與《史記·封禪書》提到的“武夷君”、齊永明三年劉顗買地券中的“武夷王”應該是指同一個神,這些説法非常正確。九店簡《告武夷》揭示了武夷神的執掌是“司兵死者”,即負責管理戰死之人。
【連劭名2017】文獻中有關“武夷”的記載很少,簡文“武夷”究竟是否指武夷山之神,不得而知,但“武夷”與“兵死”義近。《禮記·曲禮上》云:“武車綏旌。”鄭玄注:“武車,亦兵車。”夷、屍古同字。屍、死古通。《漢書·陳湯傳》云:“求谷吉等死。”顏師古《集注》云:“死,尸也。”凡爲利器所害者都是“兵死”,並不僅限於戰爭,即《尚書·洪範》所説的“凶短折”。“武夷”是陰間主司“兵死“者的神靈。
【譚梅2023】《清華簡》《九店楚簡》及馬王堆《太一避兵圖》中有共同的神名“武夷”,據傳世文獻和出土資料,從“武夷”名字的音韻以及他的神職和祭祀方法等方面看,其應即水神馮夷。武夷的神職在不同時期的文獻中產生了轉變。楚簡中武夷的主要職能是司水和管理亡魂。漢代以後的鎮墓文及買地券中,武夷司水的職能逐漸剝離,管理亡魂的神職得到延續,且增添了買地主神格。
【今按】戰國秦漢時期“武夷”職掌兵死者,與避兵有關。九店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太一避兵圖》之圖文均呈現出了古人所奉承的這種習俗。
⑤ (復)山之巸
(復)山之巸
【夏德安1998】復山是不周的別稱。
【李家浩2003】復山疑即《山海經》的“負子”。“復”可能讀爲“複”。因“有山而不合”,“缺壞不周匝”(郭璞註語),故將其中的一峰名爲“不周”;另一峰對不周山來説,是重複的山峰,故將其名爲“復(複)山”。
【工藤元男2008】傳世文獻中未見 山和復山之名。從語境來看,“
山和復山之名。從語境來看,“ (復)山之巸”與“不周之埜(野)”是用對偶的修辭法分别表現不周山的文字。
(復)山之巸”與“不周之埜(野)”是用對偶的修辭法分别表現不周山的文字。
【饒宗頤1997】“巸”可看作“ ”,猶如“沚”或“阯”。
”,猶如“沚”或“阯”。
【李零1999】“巸”讀阯。
【整理者2000】“巸”字所从“ ”“巳”皆聲符,“簡文‘巸’當以讀作‘基’爲是,‘復山之基’,猶上引《白虎通·封禪》‘梁甫之基’,即復山之山腳的意思。”
”“巳”皆聲符,“簡文‘巸’當以讀作‘基’爲是,‘復山之基’,猶上引《白虎通·封禪》‘梁甫之基’,即復山之山腳的意思。”
【連劭名2017】引釋文作“復山之熙”。“武夷”是陰間主司“兵死“者的神靈,“復山”指東北方的鬼門。《周易·復·象》云:“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人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反復即終始之道。天道運行,反復不已,終始相應。《周易·説卦》云:“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艮卦之象爲山,故曰“復山”。艮爲東北之卦,古式盤中東北是鬼門。“熙”表示南方向陽之地。殷墟卜辭中有用例,《廣雅·釋詁》云:“熙,光也。
⑥不周
【饒宗頤1997】即見於《山海經·大荒西經》等的不周之山。
【整理者2000】山名。《楚辭·離騷》洪興祖補注“《山海經·大荒西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此山形有缺,不周匝,因名之。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
【連劭名2017】指天門。古式盤中西北是天門。《莊子·庚桑楚》云:“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不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不周”當讀作“不州”,意即“不殊”,指無差異,無區別,相當於道家所説的“玄同”。“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衆妙之門”即“天門”。古式盤與天道相配,安徽阜陽西漢汝陰侯墓所出式盤,四隅有四門,分别是:西北天據己、東北鬼月戊、東南土斗戊、西南人日己。天門、鬼門都處於北方,北方爲陰,南方爲陽。
⑦兵死者
【整理者2000】兵死,死於戰爭的人。本組簡文記巫祝讓帝武夷管理兵死者,其目的是要它不爲害生人。
【李家浩2003】兵死者,指死於戰爭的人的鬼魂。
【工藤元男2008】兵死者意爲戰死者,該詞先秦文獻多見。
【劉釗2024】九店簡《告武夷》揭示了武夷神的執掌是“司兵死者”,即負責管理戰死之人。“兵死者”的字面意思是“死於兵刃之人”,在此實際是指死於兵刃之人的鬼魂。《釋名·釋喪制》説:“戰死曰兵,言死爲兵所傷也。”
【今按】兵死者,死於戰爭的人的鬼魂,兵死之鬼。《禮記·曲禮》:“死寇曰兵。”《釋名·釋喪制》:“戰死曰兵。言死爲兵所傷也。”“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死於兵者沒有資格葬入墳塋,不能享受祭饗,故而常作祟於生人;《淮南子·説林》:“兵死之鬼憎神巫。”高誘注:“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之殺。憎,畏也。”
⑧含(今)日某 (將)欲飤(食)
(將)欲飤(食)
【陳偉1998】“某”指墓主,很可能是一位“兵死者”。
【李零1999】祝辭中以“某”代稱祝者,可以任意替換。簡文內容爲祝禱武夷照顧兵死者的祝語。
【李家浩2003】據簡文“今日某將欲食”,結合包山卜筮禱祠簡,認爲“某”並沒有死,不可能是兵死者,“某”應該指病人“某”指病人。“思某來歸食故”之“某”指病人之魂。簡文內容是是爲受兵死者所害的病人招魂的禱辭。
【夏德安1998】“某”指死者,即兵死者。簡文內容爲祝禱武夷照顧兵死者的祝語。
【周鳳五2001】簡文“某”字共五見,所指稱對象都是“兵死者”。此祝禱文帶有“虛擬”的性質。
【陳斯鵬2007】“某”指兵死者,文中用“某”來代替兵死者之名,可能應是一個通用文本。九店楚簡的主體爲日書,而本篇處於日書之間,實際上也即日書的一部分,可以看作巫祝人員的參考手冊,而不是專爲某一次祝禱活動而寫的。該簡文內容爲請求武夷讓兵死者暫時脫離武夷的管轄,回到人間享受美食。
【工藤元男2008】周鳳五將“某”理解爲兵死者,解釋極爲合理。簡文是“巫祝招魂的祝禱之辭”。
【楊勇2020】簡文中的“某”指‘病人”。簡文大意爲“某”患病,通過告禱司兵死者武夷,祈求病人魂魄歸來,飲食如故。簡文用可以任意替换的“某”指代患者是因爲該文本系傳抄而來的格式化範本。獲得此範本的患者或其親屬,只需將患者的名字代入,將整個祝文口説一遍即完成了向武夷的祝禱。整個過程簡便、易行,可由患者或其家屬自行完成,不必仰賴專職的巫祝。
【今按】簡文未以實名,而以“某”代指,是該篇爲通用範本的體現。“某”有祝者、病者、兵死者等不同解讀,我們讚同整理病者説。
⑨某敢 (以)亓(其)妻上妻女(汝)
(以)亓(其)妻上妻女(汝)
【陳松長1997】釋作“某敢 (以)亓(其)妻二妻女(汝)”。“妻女(汝)”之前所闕之字在竹簡照片上依稀可辨,作兩橫劃,可釋作“二”。“妻二”即“二妻”之倒,古漢語中數詞作定語後置常見;古人之多妻,諸如堯以娥皇、女英嫁給舜帝爲妻的事亦累見不鮮。
(以)亓(其)妻二妻女(汝)”。“妻女(汝)”之前所闕之字在竹簡照片上依稀可辨,作兩橫劃,可釋作“二”。“妻二”即“二妻”之倒,古漢語中數詞作定語後置常見;古人之多妻,諸如堯以娥皇、女英嫁給舜帝爲妻的事亦累見不鮮。
【夏德安1998】死者“爲博得武夷的恩寵而同意他(武夷)以死者的妻爲妻”,然而,“這在古代中國男子死葬儀式中的程序中尚沒有其他證明”。
【李零1999】“亓妻”下殘文似非“二”字,而類似於“琴瑟”等字所从。
【整理者2000】【李家浩2003,640頁】釋作“某敢 (以)其妻□妻汝”,第一個“妻”是名詞,第二個“妻”用如動詞,是嫁給的意思。“其”指稱“某”,“汝”指稱武夷;古人有爲神祇娶妻的習俗,簡文“以其妻□妻汝”即病人許願爲武夷娶妻,把自己的妻子嫁給武夷。
(以)其妻□妻汝”,第一個“妻”是名詞,第二個“妻”用如動詞,是嫁給的意思。“其”指稱“某”,“汝”指稱武夷;古人有爲神祇娶妻的習俗,簡文“以其妻□妻汝”即病人許願爲武夷娶妻,把自己的妻子嫁給武夷。
【周鳳五2001】釋作“某敢以其妻□妻(齎)聶幣”。後一“妻”讀作“齎”,簡文意思是“某人命其妻送聶幣、芳糧給你(武夷)”,推測缺字爲“某”,用爲其妻之名的不定代詞,或者是表示恭敬的“謹”或“敬”等字眼。李家浩認爲簡文意爲病人把自己的妻子嫁給武夷的説法,不但違反人情與倫理,而且於史無徵。
【陳斯鵬2007,121頁】引釋文作:“某敢以其妻□妻(齎)女(汝)【聶】幣、芳糧,以 (量)犢(贖)某於武夷之所。”
(量)犢(贖)某於武夷之所。”
【工藤元男2008】釋作“某敢 (以)亓(其)妻□妻(齎)女(汝)【
(以)亓(其)妻□妻(齎)女(汝)【 】(聶)㡀(幣)芳糧”,與神祇娶妻相比,周鳳五所主張的“命其妻送給武夷聶幣、芳糧”這一解釋似更爲妥當。
】(聶)㡀(幣)芳糧”,與神祇娶妻相比,周鳳五所主張的“命其妻送給武夷聶幣、芳糧”這一解釋似更爲妥當。
【范常喜2009】釋作“某敢 (以)亓(其)妻上妻女(汝)”。“妻女(汝)”之前所闕之字,疑應釋作“上”。“武夷君”有可能是天神,地上的祝禱者將“某”之妻嫁於“武夷君”自然可稱是“上”。第二個“妻”字讀作“齎”並與下文連讀不可從。
(以)亓(其)妻上妻女(汝)”。“妻女(汝)”之前所闕之字,疑應釋作“上”。“武夷君”有可能是天神,地上的祝禱者將“某”之妻嫁於“武夷君”自然可稱是“上”。第二個“妻”字讀作“齎”並與下文連讀不可從。
【陳偉2009】【陳偉、彭浩2021】釋作“某敢以其妻□妻女(汝)【 】㡀芳糧”,注引李家浩2003。
】㡀芳糧”,注引李家浩2003。
【黃靈庚2011】引釋文作“某敢以其妻妻女(汝)”,簡文所載乃祭武夷神行献嬪禮也。古世祀祭天帝鬼神有行夫婦事者以爲禮目。《山海經·大荒西經》:“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郭注:“嬪,婦也。言獻美女於天帝。”嬪河之祭,殷商卜辭已有之,曰:“丁已卜,其燎于河,沈妾。”(《後编》二三·四)其風亦尙矣。《九歌·河伯》:“送美人兮南浦。”美人,河神所娶婦。祭河沈婦,類獻嬪禮。《史記·滑稽列傳》褚先生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
【林志鵬2010】簡文重新斷讀作:“某敢以其妻齎聶幣、芳糧以量(禳),贖某于武夷之所。”
【譚梅2023】《九店楚簡·告武夷》中以“某”之妻嫁與武夷,可能與楚地所流傳的河伯娶婦神話有關。
⑩ 㡀
㡀
【李零1997】九店簡“聶㡀(敝)”正是馬王堆M1簡284中“聶敝(幣)”。
【李家浩1997】九店簡“聶㡀”與“芳糧”並列,在馬王堆M1簡284中,有“合青笥二合,盛聶敝(幣)”,其中的“聶敝(幣)正與九店的”聶㡀(敝)相當。“聶幣”是指成串的絲織品碎塊。
【整理者2000】“ ”據下文而補,从“聑”得聲,讀爲“攝”,指韔、箙上的緣飾。“㡀”據下文而補,上半从采,下半从巿,“㡀”“采”二字古音十分相近。“
”據下文而補,从“聑”得聲,讀爲“攝”,指韔、箙上的緣飾。“㡀”據下文而補,上半从采,下半从巿,“㡀”“采”二字古音十分相近。“ 㡀”與“芳糧”並列,都是祭祀武夷的物品。“
㡀”與“芳糧”並列,都是祭祀武夷的物品。“ 㡀”應當讀爲馬王堆漢墓遺冊和木簽的“聶幣”,指竹笥內盛的連成串的絲織品碎块。【陳偉2009,316—317頁】【陳偉、彭浩2021,44頁】釋作“【
㡀”應當讀爲馬王堆漢墓遺冊和木簽的“聶幣”,指竹笥內盛的連成串的絲織品碎块。【陳偉2009,316—317頁】【陳偉、彭浩2021,44頁】釋作“【 】㡀”,注引整理者説。【楊華2013,389頁】“[聶]㡀(幣)芳糧”之句,李家浩指出“聶幣”指用於祭祀的絲織冥幣,已爲馬王堆漢墓M1所出遣策及竹笥物所證實。
】㡀”,注引整理者説。【楊華2013,389頁】“[聶]㡀(幣)芳糧”之句,李家浩指出“聶幣”指用於祭祀的絲織冥幣,已爲馬王堆漢墓M1所出遣策及竹笥物所證實。
【周鳳五2001】讀爲“聶幣”。馬王堆漢墓隨葬品所見的泥郢稱是金鈑的象徵物。“攝”似當取“攝位”“攝代”之意,“幣”是“幣帛”,“聶幣”(成串的絲織品碎片)每一片代表一匹繒帛,它與泥郢稱等都是財富的象徵,屬於隨葬的明器。
【劉信芳2011】隸定作“
 ”,指成串的錢幣。
”,指成串的錢幣。
【工藤元男2008】無論其實際形態如何,它應該是祭祀武夷的物品。
【今按】馬王堆漢墓遣冊和木牌(揭)書有“聶敝”“聶幣”:一號墓遣冊284:“青笥二合,盛聶敝。”整理者(1973,152頁)注:“敝”即“幣”字,竹笥木牌正作“幣”。聶幣,即布帛的碎片。一號墓出土337號竹笥繫有“繒聶幣笥”木牌,346號竹笥旁有“麻布聶幣笥”木牌,兩竹笥內均盛絲織品碎塊一串。三號墓遣冊385:“聶敝二笥。”整理者(2004,71—72頁)注:“敝與幣通。聶即牒,意即碎片。馬王堆一、三號漢墓均有土金、土錢、聶敝的記載,可以推定它們分別是指金、銅、布帛三種質地的貨幣,或可充作貨幣使用的物質。聶幣當爲以布帛碎片作爲冥幣。”李家浩所言九店簡“聶幣”指用於祭祀的絲織冥幣,既爲馬王堆漢墓遣冊、木牌、實物所證實,又與九店簡祝禱辭以“聶幣”作爲進獻司兵死者武夷的語境吻合。“聶幣”相當於冥幣的功能學界認同度較高,但對於形製仍有不同意見,周世榮(1992)“聶幣”即絲織品的碎片,之所以被稱爲“聶幣”,是因爲它象徵楚國的貨幣“金鈑”。李零(1997)、夏德安(1998)同意該説。周世榮(2001)進而指出聶幣是被分割成片(幅或段)的布帛類貨幣。撕裂後的布帛,不能再作衣料,實際上是專門用作交易的。而“束帛”則是“聶幣”之一種。實際生活當中必然有實物“聶幣”存在。朱德熙、裘錫圭(1982)則認爲“謂聶幣之聶意即碎片,是可疑的”。陸錫興(2016,348—350頁)先秦、漢,“攝”之代替意義常見,馬王堆漢墓中“聶”爲“攝”之古字,當爲代的意思;“聶幣”意爲“代幣”,以零碎絲織品代替正式的幣帛是事鬼神的幣帛,象徵而已。陸錫興對“聶幣”的解釋實際上綜合了“聶”的碎片與代替之義。
⑪芳糧
【整理者2000】芳糧、 㡀並列,都是祭祀武夷的物品。
㡀並列,都是祭祀武夷的物品。
【周鳳五2001】芳糧即《離騷》之“椒糈”,是以香料調製,用來招請或祭祀鬼神的芬芳米糧。
【楊華2013】芳糧,當讀爲“烹糧”,即煮熟的飯食。古代“糧”指軍糧或其他行到所用之糧。《告武夷》爲招“兵死者”之魂而作的祝禱之詞,讓這些戰死疆場的遊魂野鬼享用他們生前熟悉的軍用伙食,也是很合適的。
【今按】“芳糧”與“ (攝)㡀(幣)”並列,均爲祭祀敬獻武夷之物,而非用於兵死者享用。古人有以精美食糧作祭品的習俗,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馬禖》簡157背:“大夫先㪇<牧>次席,今日良日,肥豚清酒美白粱,到主君所。”
(攝)㡀(幣)”並列,均爲祭祀敬獻武夷之物,而非用於兵死者享用。古人有以精美食糧作祭品的習俗,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馬禖》簡157背:“大夫先㪇<牧>次席,今日良日,肥豚清酒美白粱,到主君所。”
⑫

【夏德安1998】讀作“量育”,意爲“儲存食品”。
【整理者2000】似是祭名,應讀作“詳讀”或“揚讀”;“詳(揚)”“讀”同義,故可連説。【陳偉2009】
 (犢),疑讀爲“揚讀”,訓爲“説”。
(犢),疑讀爲“揚讀”,訓爲“説”。
【周鳳五2001】讀作“量贖”,“量”即“衡量輕重”,“贖”即“以金錢贖罪”。“量贖”即“衡量犯罪情節輕重,交付等值的金錢以免除罪責”。
【陳斯鵬2007】引釋文作“ (量)犢(贖)”,“贖”即贖罪。
(量)犢(贖)”,“贖”即贖罪。
【工藤元男2008】整理者祭名説、周鳳五量贖説“殊難判斷,姑且看作祭祀名。
【林志鵬2010】“量”疑讀作“禳”,“犢”當從周風五讀作“贖”,“量(禳)”“贖”分屬兩句,簡文當讀爲:“某敢以其妻齎聶幣、芳糧以量(禳),贖某于武夷之所。”
【范常喜2009】周鳳五讀“ ”作“量”至確;上博簡出現幾例與“
”作“量”至確;上博簡出現幾例與“ ”字相關的“量”字,爲“
”字相關的“量”字,爲“ ”字的釋讀提供了新線索。楊澤生對上博簡《競建內之》中的“量”字有很好的訓釋,他認爲祭祀時,不同的祭祀物件其選擇的祭品往往不同。周鳳五訓“
”字的釋讀提供了新線索。楊澤生對上博簡《競建內之》中的“量”字有很好的訓釋,他認爲祭祀時,不同的祭祀物件其選擇的祭品往往不同。周鳳五訓“ ”爲“贖”也最爲合理,不過並非指“以金錢贖罪”,而是奉上一定數量的“聶幣、芳糧”將“某”之魂魄贖回。林志鵬“量贖”訓釋雖過於迂曲,但斷句正確可從。此句當重新斷作:“[
”爲“贖”也最爲合理,不過並非指“以金錢贖罪”,而是奉上一定數量的“聶幣、芳糧”將“某”之魂魄贖回。林志鵬“量贖”訓釋雖過於迂曲,但斷句正確可從。此句當重新斷作:“[ (聶)]㡀(幣)芳糧
(聶)]㡀(幣)芳糧 (以)
(以) (量),
(量), (贖)某於武夷之所。”
(贖)某於武夷之所。”
【陳偉2009】
 (犢),疑讀爲“揚讀”,訓爲“説”。
(犢),疑讀爲“揚讀”,訓爲“説”。
⑬向
【整理者2000】釋作“昔”,原文爲省形字,是“夕”的假借,訓爲“夜”。【楊華2005】釋作“昔”,“昔”即“夕”,意即武夷神今夜享受某人的聶幣、芳糧之後,誠懇地希望你能讓某人之魂歸來,飲食如故。這是一篇祭禱鬼神,進行招魂的祝禱辭。從其口氣來看,祝禱的儀式無疑也是在夜間舉行的。【工藤元男2008,56—57頁】釋作“昔”,讀爲“夕”。
【顏世鉉2000】釋作“襄”,讀爲“曩”,指前不久。
【周鳯五2001】釋作“向”,讀爲“曏”,即“曩”,指不久以前,引申爲“昔日”之意。簡文斷讀爲“君向(曏)受某之 (攝)㡀(幣)芳糧”,語譯爲“您已經接受過‘某’的攝幣、芳糧了”。
(攝)㡀(幣)芳糧”,語譯爲“您已經接受過‘某’的攝幣、芳糧了”。
【冀小軍2002】釋作“皿”,疑讀爲“饗”。簡文“饗受”,即《潜夫論》中的“受饗”。
【陳斯鵬2003】釋作“向”,疑讀“饗”,義爲飲饗、受食。
【陳偉2009】釋作“向”,讀爲“饗”。
【范常喜2009】釋作“向”,讀爲“享”或“饗”,意謂鬼神享用祭品。此句當重新斷讀作“君向(享),受某之 (聶)㡀(幣)芳糧”。“君向(享)”與“受某之
(聶)㡀(幣)芳糧”。“君向(享)”與“受某之 (聶)㡀(幣)芳糧”可能兩句意思相當,均是籠統地指武夷君享用了“某”送給的所有祭品(含妻子),當然,“君向(享)”也可能僅是指享用“某”奉上的“妻子”而言。冀小軍釋作“皿”雖不可從,但讀作“饗”卻十分正確,不過連下文“受”字,認爲簡文中的“饗受”即《潜夫論》中的“受饗”則不可從。
(聶)㡀(幣)芳糧”可能兩句意思相當,均是籠統地指武夷君享用了“某”送給的所有祭品(含妻子),當然,“君向(享)”也可能僅是指享用“某”奉上的“妻子”而言。冀小軍釋作“皿”雖不可從,但讀作“饗”卻十分正確,不過連下文“受”字,認爲簡文中的“饗受”即《潜夫論》中的“受饗”則不可從。
【今按】“向”,圖版作“ ”,字形不清。有“昔”“向”“皿”“襄”等不同的隸定意見。今隸定從周鳳五作“向”,訓讀從范常喜讀作“享”。
”,字形不清。有“昔”“向”“皿”“襄”等不同的隸定意見。今隸定從周鳳五作“向”,訓讀從范常喜讀作“享”。
⑭囟
【李零1999】應讀爲“思”。【整理者2000,109頁】“囟”屢見於楚簡,《説文》説“思”从“囟”聲,故楚簡文字“囟”有時又寫作“思”。跟楚簡用法相同的“囟”字還見於周原甲骨刻辭,都應當讀爲“思”,表示希翼。”【工藤元男2008,57頁】
【陳斯鵬2003】【范常喜2009】【陳偉2009】【陳偉、彭浩2021】【劉釗2024】讀爲“使”。
【今按】“囟”字楚簡常見,意爲“使”,陳斯鵬有詳細論證。
⑮某
【整理者2000】【李家浩2003】“某”應指“病人之魂”。【工藤元男2008】【陳偉2009】【陳偉等2021】【楊勇2020】等從之。如【工藤元男2008】“令某魂歸來,飲食如故”從李家浩之解釋,《告武夷》篇乃巫祝招魂的祝禱之辭。
【周鳳五2001】篇中所見稱代詞用法一致。“某”字共五見所指稱的對象都是“兵死者”,沒有例外。至於職司禱祠的巫祝,在《告武夷》篇中並沒有現身。【陳斯鵬2007】從之:兵死者的妻子用“聶幣”“芳糧”爲兵死者贖罪,請求武夷讓兵死者暫時脫離武夷的管轄,回到人間享受美食。
⑯逨
【整理者2000】【李家浩2003】簡文“來歸”可證明《楚辭》古文當作“來歸”。“來歸”句與《楚辭·大招篇》之“魂乎歸徠、以娯昔只”、《招魂篇》之“魂兮歸來”等字句十分類似,簡文“來歸”爲招魂之辭、即巫祝呼喚病人離散之魂(某)的詞語。
【工藤元男2008】“來歸”即是見於《楚辭》的《招魂》《大招》篇的“魂乎歸來”。該篇是“巫祝招魂的祝禱之辭”,李家浩(2003)指出了九店楚簡《告武夷》篇乃巫祝招魂的祝禱之辭,這就使得卜筮祭禱簡與包括《告武夷》篇在內的九店楚簡《日書》之間的継承關係得到具體確認。
⑰〖如〗故
【李零1999】引釋文作“故□”,“故”下應補“人”字。
【整理者2000】釋作“故□”,注曰“故”之下有類似“八”字形的筆畫,是殘文還是表示文字完結的符號,待考。【陳偉2009,316頁】【陳偉等2021,44頁】從整理者,釋作“故□”。
【李家浩2003】“故”字之下,原簡有筆劃,似是表示文字完結的符號。據韻腳“野”“者”“汝”所”“故”,“故”字之上,可能是漏寫或省略“如”之類的字。【工藤元男2008】【范常喜2009】從之,文意解讀或釋文增“如”字,作“如故”。
【周鳳五2001】李家浩説法可從。無論補字與否,“故”字都可以理解爲雙關語,既指兵死者生前,又指其接受祭祀的先例。
【陳斯鵬2007】對“故”及其後是否存文存疑,引釋文作“故(?)□(?)”。
【劉釗2024】釋作“故”。
编辑:赵露晴 初审:刘雯 复审:俞林波 终审:张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