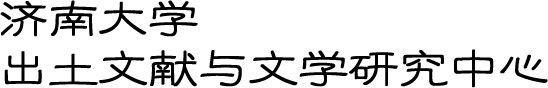丝绸之路上的简帛书写
蔡先金
(聊城大学简帛学研究中心,山东省特色文献与传统文化“双创”协同创新中心)
在今天“一带一路”的语境下,“丝绸之路”愈加彰显其熠熠光辉。穿越时间隧道,人们当下仿佛又看到汉唐以来丝路上络绎不绝的商团,听到洒落于戈壁沙滩上驼队铃声,恢弘大气,超以象外。众人皆知,“丝绸之路”这个闪光的概念是19世纪著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男爵提出的,恰巧紧接19世纪末以来,各色人种探险队往来于我国广袤的西域,发现了大量的“流沙坠简”,由此又催生了“简帛学”这一国际显学。由此可知,“丝路”与“简帛”就成了一对相互关联的关键性概念。聊城大学文学院的简帛学研究团队于2018年甫一成立,诸位同仁不甘落后,志存高远,第一次学术“预流”计划就是从“丝路”与“简帛”关联课题开启,对“丝绸之路”作阶段性的简帛文化地理和知识考古学的田野考察,旨在考察与了解“丝绸之路上的简帛书写”之状况。不论其想法与行动是齐庄公眼中的“螳臂当车”式的“天下勇武”,还是世人心中“全狮搏兔”般的“亦尽全力”,诸位研究团队成员都毅然决然地参与实施西部简帛出土遗址考察计划。
2018年8月6日至15日,考察团队一行11人,历时10天,纵横千万里,可以烈日下数次徒步戈壁荒滩10余里,可以穿越墓冢地深入低矮阴森之古墓,可以爬上火焰山寻找遗址地点而消失在众人视线之外,可以自助就餐于乡间简陋之屋舍,可以会讲于长途旅行的中巴上,可以捡拾废弃的残砖碎瓦而视作珍宝,可以用手触摸遗址残壁断垣而与古人作交流状,可以围绕遗址周边作朝圣般的行走,可以夕阳下汽车抛锚于路途上而集体战胜困难,可以在大河畔、大漠旁、大道边、戈壁中……经过这些无数的“可以”,最终圆满完成了既定的田野考察计划目标。当考察接近尾声时,仍在旅途的队员们回顾来时路,既有考察收获的喜悦,也有人生感动的哽咽,可谓学满于路,情满于路,留下了一个个值得回忆的美好故事。全体团队成员,做事持敬,为人心诚,以高尚和智慧的力量开启了神圣的简帛学术之旅。单从“丝路——简帛”角度,通过这次实地考察,考察团队成员起码可以获得这样一些印象。
一、丝绸之路与简帛之路重合
如果说“丝绸”是一种物质符号的话,那么“简帛”显然就是一种知识的符号。历史上商贸大通道很多,为何唯有“丝绸之路”获此殊誉?因为丝绸之路承担的不仅仅是货物贸易,还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可以说是前“全球化”的一种“区域化”试验场,这里包括贸易开放、资金流动、人员往来、文化整合等因素。这也可以从“丝绸之路”概念形成过程中获得更好的理解。李希霍芬起初在商贸意义上真正要说的是“丝绸贸易”,在《跨越中亚的古代丝绸贸易商路线》(The Ancient Silk-Traders’ Route across Central Asia)(1878)一文中就是使用“丝绸贸易路线”一说,所以,中国“西北考察团”中的早期学者,如黄文弼、陈宗器等对于这条道路的理解与称谓,最合于李希霍芬的原意,黄文弼称作“贩丝之道”,陈宗器称作“运丝大路”。今天,在用词上最微妙的改变,是去掉了“贸易”二字,固定为“丝绸之路”,具有了超越贸易活动的更加宽泛含义的可能,这更适合于对于这条路的命名以及后人对于这条路的理解。丝绸所到之处,也就是简帛所到之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简帛作为文献载体运用于丝绸之路上。二是简帛作为载体记载有关丝绸之路内容。丝绸之路上简帛的大量出土,已经说明第一种情况的存在。其实在丝绸贸易过程中,很难说没有用贸易丝绸作为记载文字或图画内容的载体,只是湮埋在历史尘埃中而已。已发现的简帛,记录丝绸之路上相关内容的可谓比比皆是。敦煌悬泉置是连接东西方的驿站,悬泉汉简中记载了丝绸之路上中西交往的盛况,过往悬泉置的人员有西域各国使者宾客,如大月氏、大宛、康居往来交往的记录,反映出河西走廊是各民族、各色人种交流和融合的历史舞台,是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北方塞人的游牧文化、本地农耕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区域。张德芳认为,西北汉简堪称是一个历史文化宝藏,为研究丝绸之路提供了生动翔实的原始资料,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很多学科领域,所以“西北汉简从广义上讲都跟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简帛所到之处,可以说就是华夏族文化泽被所至,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信物所在。探访简帛传播之路,也就是在探寻伟大的丝绸之路。
二、古建筑遗址与简帛遗场重合
汉帝国公用建筑有驿站,其邮驿系统是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传或置;有长城关隘及障塞烽燧、粮仓,组成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如新疆境内的烽火台就是最好的例证。新疆的烽燧遍布天山南北,它们与丝绸之路中道与北道走向一致,起到了护卫丝路畅通的重要作用。这些古建筑遗址中几乎都发现了简帛,无论是文书还是启蒙书籍,无论是儒家经典还是方技术数,都说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般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文化知识生活的世界。马圈湾遗址为西汉玉门关候官治所,出土简牍1221枚;悬泉置创建约在西汉武帝元鼎年间,延续近400年,出土简牍35000枚与帛书10幅;肩水金关(A32)出土简牍11850枚;肩水都尉府(A33地湾)出土简牍2000枚;肩水候官(A35大湾)出土简牍2615枚;甲渠候官破城子(A8)出土简牍12931枚。每一个重要的建筑遗址,都抵抗了千年的风雨侵蚀,凡是留存的遗迹都是时光雕刻出来的历史雕塑,令人肃然起敬,并产生无限的遐想。每一处遗迹,那千年以前的人们使用过的陶器碎片,都诉说着湮埋在时间深处的历史故事。近代以来的探险家、考古学家探掘过这些遗址,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科兹洛夫、瑞典的斯文·赫定与贝格曼、日本的大谷光瑞与橘瑞超,并将西部简牍带到了世界各地,如今仍旧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图书馆、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这些古建筑遗址与简帛遗场重合,说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之昌盛。
三、简帛书写是文化书写
简帛书写作为一个个鲜活的文本书写,无论文本之内还是文本之外,都附有文化信息与知识,由此简帛书写亦是文化书写,承载着历史、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军事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内容。每一枚竹简,每一片削衣后留下的秭,每一幅缣帛,都有可能书写着一个宏大叙事,一个天大秘密。悬泉置出土的《元致子方书》帛书,既是一封平常的书信,又是一个文化书写。察看其文本书写,就会发现当年佣书与自书同时存在,发现当年书信的“书仪”格式,发现信中提到人物之间的社会交往,发现当时人们的一般日常生活场景,发现当时人们信息传递的邮驿系统。悬泉置出土的“过长罗侯费用簿”,记载了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在接待长罗侯常惠的使团第五次过往悬泉置去乌孙国商讨和亲时,在悬泉置的过往人数和所消耗的食物数量等事宜。由此可以遥想当年常惠使团到达悬泉置的热烈场景。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在乌垒(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策大雅南)设都护府,维护西域地方的社会秩序,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都护府统管着大宛以东、乌孙以南的30多个国家,各国“自译长、域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确认是汉的官员,万国来朝成为时尚,悬泉置始终车水马龙。由此看来,面对简帛这些文化宝藏,今人并不可以用简单的一般书写眼光来看待简帛书写,这里既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也记录下了相关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简帛学研究西部考察团队的每位成员,在考察期间都会产生不同的感动与感悟,陷入不同的沉思与追问,但团队成员追求高尚的情怀是相同的,学术精神是相通的,感情交流是顺畅的,坚强意志是共同的,未来愿景是美好的。这次考察活动,既是简帛学研究一次田野考察,也是团队精神的一次洗礼,更是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人人会有选择,但选择是有标准的。简帛学研究团队成员既然选择了一条简帛学研究之路,那就像这次考察一样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只要有行动,就会有故事,就会越来越接近心中的远方;纵然可能会像考察中遇到的境况那样,有戈壁荒滩,有沙漠尘暴,有崎岖小径,有艰难险阻,但是团队成员永远看到的是路边的风景,内心感觉到的是那份坚毅的意志与审美的感受,收获的永远是美好的回忆和付出后的喜悦。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问,一个学术团队有一个学术团队之精神。简帛学研究团队成员充分理解“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之警言,无论古今,在学术上力争做到先“为己”,后“为人”。倘若将学术之旅比作长征的话,那么这个学术团队才刚刚动身起步,这次学术田野考察,也最多只能视作为简帛学研究团队成立举行了一个奠基礼。“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阳关大道,前景广阔!
编辑:赵露晴 初审:刘雯 复审:俞林波 终审:张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