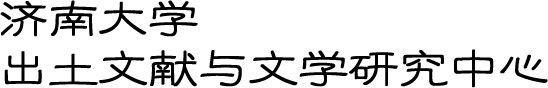第一章 總論
引言
中國文化乃是世界文明的重大組成部分,而中國文學又居其一。倘若說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的話,那麽中國古代文學在華夏民族形成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從某種角度來說,華夏民族的性格與品質就是中國文學的一種呈現,反之亦然;而一部華夏民族史又與中國文學史互爲同構,以至於德國哲學家康得•凱瑟琳(Count Keyserling)高度讚歎:“古代的中國,他們苦心經營,完成最完美的社會形態,猶如一個典型的模範社會……中國創造了爲今日人們已知的、最高級的世界文明……中國人高雅的風采,在任何環境裏,都是表露無遺。……也可以說,中國人,是所有人類中最有深度的人。”中國古代文學具有輝煌的成就,足以彪炳千古,而今簡帛文獻屢有發現,愈益爲之豐富與添彩。
簡帛文獻唯我中華之獨造,而“書於簡帛”乃可傳承華夏之文脈。地不愛寶,20世紀可以說是一個簡帛大發現的世紀。天不喪斯文,簡帛文獻大量出土,世人驚奇,學界震動與歡呼。據統計,自20世紀至今,國內有關簡帛的發現已達百餘次,出土地點涉及17個省區,出土簡帛已達30餘萬枚(件),如上世紀末漢代懸泉驛遺址一次出土簡牘35000餘枚、帛書10件,本世紀初裏耶一次出土36000餘枚。據不完全統計,流失海外簡牘約有111000餘枚。1903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發表《中亞與西藏:前往聖城拉薩》(Central Asia and Tibet:Towards the Holy City of Lassa,2vols,London.),可謂西人簡牘考古研究之起始。1914年,羅振玉、王國維出版《流沙墜簡》,開中國近代研究簡牘學之先河。1944年,蔡季襄石印《晚周繒書考證》,可謂帛書研究嚆矢之作。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簡牘與帛書的研究已經成爲海內外學界所關注的一門“顯學”,號稱“簡帛學”。 這亦恰與王國維的著名論斷若合符契:“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
簡帛出土及其文獻之研究,直接推动20世90年代学界产生了“走出疑古時代”之念头,這主要是因爲“很多久已亡佚的先秦古書得以重見天日,不少傳世的先秦古書有了比傳世各本早得多的簡帛古本,古書中很多過去無法糾正的錯誤和無法正確理解的地方得以糾正或正確理解,不少被普遍懷疑爲漢以後所僞作的古書得以證明確是先秦作品,不少曾被普遍認爲作于戰國晚期的古書得以證明是戰國中期甚至更早的作品,先秦古書的體例也被認識得更清楚了。”
近年來,簡帛學漸成顯學的同時,相關研究更是方興未艾。文史學界當然不堪落後,紛紛“預流”,有學者甚至期望“改寫古代文學史”或“重寫古代文學史”,以便“帶動傳統文學史研究領域的突破性進展”。簡帛學研究形勢喜人,形勢逼人,在此背景下,簡帛文學研究理所當然地提到了學界的議事日程。
第一節 簡帛文獻與簡帛文學概念及其分類
在思考問題或從事課題研究的時候,我們是不可能離開必要的概念的,而且每個概念的重要程度卻又是有所不同的,尤其是那些關鍵性的概念是必須界定清晰的,否則我們的思考或者我們的學術研究就可能無法進行下去了。“建立概念是我們認識世界、處理日常生活的途徑,我們掌握和發展概念的目的就是爲了能夠獲得人和事物的意義,並與他人進行交流。顯然,其中有些概念比另外一些概念更加重要。那些關鍵概念使得我們能夠探索各種各樣的情境和事件,尋找到有意義的聯繫。”清晰的概念是清晰思维的基础性条件,而弄清楚关键概念亦非易事,但是我們研究问题又繞不過去,所以界定概念是一項必要的工作。
一、出土文獻與簡帛文獻概念
在理解簡帛文學概念之前,我們首先應該弄清楚文獻、出土文獻與簡帛文獻之概念。“文獻”一詞最早見於《論語•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也。’”用“文獻”自名其著述,起于宋末元初的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馬氏還對於“文獻”一詞予以了界定:“凡敍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在傳統古典文獻學領域,文獻的定義重要的是指向內涵,即典籍的記載與宿賢的言論,這可能是詞源考稽的結果。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文獻學界對於“文獻”之定義有所發展,重要是指向載體。1983年我國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文獻著錄總則》(GB3792.1-83)給“文獻”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是:“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由此定義出發,“文獻起源之早,可謂與人類知識萌生同步,而後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之中,乃構成了人類全部知識學重要基礎條件之一。”然而,從不同的角度,文獻的分類是不同的。從傳世或出土的角度,我們將古典文獻分爲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傳世文獻當然就是古代流傳下來的文獻,相對于傳世文獻來說,正規考古挖掘或非法盜掘出土的文獻那就是出土文獻了。當然也有学者从广义与狭义双重角度去理解,“廣義的出土文獻是相對于傳世文獻而言的,即考古發掘出土的(或經過鑒定、來源明確的館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獻’。”“狹義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書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書),主要是指上個世紀大量出土的簡牘、帛書和紙質文書等。”我們在此選擇從狹義而非廣義上去理解與使用出土文獻概念,既是從廣義角度去界定出土文獻,亦勢必將其與“出土文物”區分開來。出土先秦、兩漢時期的文獻,即爲上古出土文獻。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既然都是文獻,那麽我們就應該平等對待,不能採取厚此薄彼的歧視之態度。
用來記錄文獻的物質材料是文獻載體。在出土文獻中,倘若按照載體分類的話,出土文獻又可分爲甲骨文獻、青銅文獻、簡帛文獻、玉石文獻、紙質文獻等。由此看來,以簡帛作爲載體的文獻就可謂是簡帛文獻。但是,簡帛文獻自漢至今廣有出土,有的經過時間的推移,人們已經視同傳世文獻,如《穆天子傳》,而且開展了廣泛的研究。因此,我們研究的簡帛文獻也大抵是指20世紀以來發現的文獻,這樣也就解決了我們課題研究中對於簡帛文獻選擇的問題。
二、簡帛文獻的分類
簡帛文獻按文獻載體可以再細分爲簡牘文獻與繒帛文獻。
(一)簡牘文獻
在紙張發明之前,竹木是使用最廣泛、最普遍的書寫材料。甚至在紙發明以後數百年間,簡牘仍繼續用作書寫材料的載體。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曰:“書契之用自刻畫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爲後先,而已竹木之用爲最廣。竹木之用亦未識始於何時。”簡牘既是簡與牘的合稱,又常常統稱爲“簡”。簡有竹簡和木簡之分。截竹爲筒,破筒爲片,稱爲“簡”,這些若干簡編聯在一起稱爲“冊”。槧木截取,削成版片,稱爲“劄”或“牘”,又稱“方”或“版”。許慎《說文解字•竹部》曰:“簡,牒也。”又:“牘,書版也。”段玉裁《注》曰:“按簡,竹爲之;牘,木爲之。”王国维曰:用竹者曰册,曰简,用木书者曰方,曰版,竹木通谓之牒,亦谓之札。明人宋應星《天工開物》記載“殺青”曰:“身爲竹骨與木皮,殺其青而白乃見,萬卷百家,基從此起,其精在於此,而其粗效於障風、護物之間。”“所謂殺青,以斬竹得名,汗青以煮瀝得名,簡即已成紙名,乃煮竹成簡。”秦时牘之製作可入律,《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司空》記載:“令縣及都官取柳及木柔可用書者,方之以書;無方者乃用版。其縣山之多菅者,以菅纏書;無菅者以蒲、藺以枲削之。各以其獲時多積之。”由此看来,簡牘作爲文獻載體,書之於竹稱之爲“簡”,而記之於木稱之爲“牘”。至漢代,許慎已將“簡牘”混用,竹或木之書寫材料,均可混稱之爲“簡”了。簡與策又有別,《儀禮•聘禮》賈公彥疏:“簡謂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春秋左傳》孔穎達疏:“單執一劄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其實,簡又可作泛稱,而非僅指一片劄。簡牘或在殷商即已出現,商人曾自稱“惟殷先人,有典有冊”(《尚書·多士》,但因年代久遠至今沒有發現簡牘實物。迄今出土簡牘文獻主要集中于戰國至漢、晉時期。東晉以後,紙張基本取代簡牘,雖然簡牘有間或使用但已非主流。簡牘作爲文獻載體,較之金石有其取材容易、便於書寫以及重量輕等優點。故自有簡牘作爲文獻載體以來,著作較前大增。我國“軸心期”乃至以後的漢代著作,大都是以簡牘作爲載體。但是,簡牘作爲書寫材料也有其明顯之不足,如分量重,體積大,易蟲蠹,閱讀、收藏、攜帶都極爲不便,弄亂了更不易整理。
(二)繒帛文獻
繒帛,是絲織文化之産物,起源於中國。絲織物在戰國以前稱爲帛,秦漢以後稱爲繒,合稱則爲繒帛。記錄知識的絲織品常被稱爲帛書,或稱爲繒書,而古人又稱用白色帛書寫者爲“素書”,如東漢《太平清領書》皆用縹白素;用黃色帛書寫者爲“黃書”,如東漢張陵用以傳授房中儀軌之書就是以“黃書”爲名。帛書始於何時已不可考。郭沫若認爲:“商代除了甲骨文之外,一定還有簡書和帛書。”從文獻記載來看,至遲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帛書,如《晏子春秋•外篇》雲:“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榖,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邑。”由此看來,大約西元前7世紀就已經使用帛書了。又,《論語•衛靈公》記“子張書諸紳”;《墨子•明鬼》載“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儀禮•士喪禮》記“爲銘各以雜物,亡則以緇”;《國語•越語》記“越王以冊書帛”;《韓非子•安危篇》記“先王寄理於竹帛”,亦可爲佐證資料。迄今爲止,我們能夠目睹最早的帛書實物是戰國中晚期的湖南長沙子彈庫楚帛書,也稱爲“楚繒書”。1942年,這些“楚繒書”是在子彈庫戰國楚墓中被盜掘出土的,現藏美國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因此,王國維認爲:“帛書之古見於載籍者,亦不甚後於簡牘。……以帛寫書,至遲亦當在周季。”帛書起源何時,尚無定論,但從文獻記載看,春秋時期應該已經有了。絲織品作爲文獻載體有輕柔、便於剪裁、易於卷舒等優點,但其珍稀昂貴、易腐朽,故繒帛文獻出土相對較少。
簡帛文獻的分類已經清晰了,但是我們並不是將它們作爲研究物件,只是選擇其中的一部分,選擇的標準大抵是:一是具有文學性的作品;二是近代以來出土或發現的上古文獻。
三、簡帛文學概念
“文學”一詞,從春秋戰國至漢,其含義經過廣狹多次的變更,略有辯說、文辭、學術、官名、經學等多種含義,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學東漸之後方才指西方所謂的純文學,或者說指現代學科分類中的文學學科。簡帛文獻中“文學”一詞雖然常見,但與傳世文獻中的“文學”含義相比並無二致。“簡帛文獻有各種類型,很多文獻都有它們特定的性質和內容。雖然它們都有一定的‘文獻’性質,但是並非所有的簡帛文獻都有‘文學’意味。”“古人雖然未嘗致意于作文,但是發言立意往往有‘文學’意味。”“這就需要我們對簡帛文獻中的‘文學’性因素進行篩選。說白了,我們需要的是‘文學’而非‘文獻’,因此不能網羅無遺,細大不捐。……我們既然強調‘文學’性,在簡帛文獻中理所應當選擇那些帶有一定‘文學’色彩的‘美文’才好。”
中國古代文獻浩如煙海,其中流傳下來的可謂傳世文獻,而埋藏地下後又出土的可謂之出土文獻;傳世文獻中包含的文學作品,可謂之傳世文學,出土文獻中包含的文學作品,可謂之出土文學。當然,兩者之間不可能截然分開,我們也不可能以非黑即白的簡單思維去對待這兩個概念。這僅是一個大體分類,以便於研究使用而已。按照文獻載體分類,簡帛文獻中包含的文學作品,又可謂之簡帛文學。
在中國文學分期中,上古期是指先秦兩漢時期,上古文學即指先秦兩漢文學。上古時期是人類歷史上最爲漫長的時代,上古文學則是中國文學的源頭,詩歌、神話、散文、辭賦等各種文體都在這一時期形成,古代文學的主要特徵也在此時期奠定。作爲中國文學的孕育、萌芽時期,上古文學自有其獨特的意義與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上古時期距今久遠,其開端又難以考證,使得這一歷史階段的資料稀少而珍貴,歷代學者雖汲汲于上古文學的研究,但仍存在諸多空白。若要填補這些空白,進一步完善上古文學研究體系,可以依靠地下所存之上古文學資料。簡帛文獻中發現的文學作品大都屬於上古文學範疇,這爲上古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提供了新的視角。
四、簡帛文學的分類
簡帛文學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分類,從歷史分期角度,可以分爲簡帛東周文學、簡帛秦代文學、簡帛漢代文學;從雅俗角度,可以分爲簡帛雅文學、簡帛俗文學;從文體角度,可以分爲簡帛神話傳說、簡帛詩歌、簡帛辭賦、簡帛散文、簡帛古小說等。通過對詩歌、神話傳說、辭賦、散文、古小說等簡帛文學文獻的專題研究,我們可以觀見這些文學類型在上古時代的真實發展脈絡。因此,在整理簡帛文學作品的基礎上,分析與研究這些作品中的文學因素及其文學價值,無疑既有補于傳世上古文學研究的不足,又有利於構建簡帛文學研究的框架體系。
(一)簡帛詩歌
簡帛詩歌主要包括簡牘文獻中的“逸詩”、稱引“詩”、阜陽漢簡“詩”、敦煌漢簡“詩”以及“論詩”的上博簡《孔子詩論》。所謂“逸詩”過去主要是指爲“詩三百”整理者所刪之詩,現則擴展至殷商至戰國時代産生的記錄在傳世文獻或簡帛文獻、而未見於今本《詩經》的詩之篇、章、句,如上博簡《多薪》、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稱引《詩》中的語句是古代文人論理言說的常用方式。所謂“稱引詩”,就是稱《詩》之篇名,引《詩》之章句,如郭店簡《緇衣》《五行》《唐虞之道》《語叢三》中涉及到的引《詩》。阜陽漢簡《詩經》有170餘片,篇目有《周南》《召南》《邶》《墉》《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曹》《幽》十四國風65首殘文及《小雅》《鹿鳴之什》4首殘文。胡平生、韓自強將阜陽漢簡《詩經》與今本《詩經》及今已亡佚的魯、齊、韓三家《詩》做了比勘,認爲它不屬於魯、齊、韓、毛中任何一家《詩》的傳本,“是否與《元王詩》有關也無從考證”,因此“只好推想它可能是未被《漢志》著錄而流傳於民間的另外一家”。上博簡《孔子詩論》是目前最早的一部詩學專著,內容都是有關《詩》的評論,充分反映出儒家詩學思想和美學思想。
簡帛詩歌價值很高,既是古人寶貴的詩歌文學寶藏,又可以彌補上古詩歌傳世之不足,還可以幫助解決一些有關上古詩歌的學術公案。
(二)簡帛神話傳說
神話是遠祖留給後人的最爲寶貴的文化遺産,自從誕生之日起,就注定神話要在人類精神世界中佔據尤爲重要的地位。它滲透了先民的情感體驗,包含著先民的智慧和思考,體現了先民的意志,是先民通過幻想和想象“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神話總是那么瑰麗与神奇,吸引着人們对其不断地探究。簡帛文獻又提供了一些新的神話文本及其神話傳說材料,進一步豐富了我國神話園地。簡帛的神話傳說主要有長沙子彈庫《楚帛書》記載的創世神話、上博簡《子羔》篇記載的感生神話、王家台秦簡《歸藏》記載的嫦娥神話、睡虎地秦簡《日書》記載的牽牛織女神話以及《幽公盨》、《容成氏》記載的有關大禹的神話傳說。《楚帛書》是迄今見到的唯一的上古創世神話文獻,爲我們描述了一幅上古創世神話圖景,同時也打破了西方人對於中國無創世神話的妄說。上博簡《子羔》篇是以集群形式記載了上古感生神話。1993年王家台秦簡《歸藏•歸妹》出土,其中卦辭記載了嫦娥神話的文本雛形,將嫦娥神話的文本記錄年代提前至戰國時期。1975年,在湖北省雲夢縣的睡虎地11號墓出土了秦簡《日書》甲種,《日書》爲戰國晚期的蔔筮一類的書籍,記載了牽牛織女神話故事的相關資料,價值有三:(1)將牽牛織女婚戀神話的文獻記錄時間提前到了戰國時代,可以肯定的是,其形成時間肯定會早於此。(2)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該神話的原初狀態:牽牛織女的婚姻是一個悲劇,其原因就在於織女被牽牛多次抛棄,並不像是後世典籍記載和民間口頭傳說中的對於不朽愛情的謳歌和頌揚。(3)牽牛織女神話衍生于秦文化發祥地。上博简《容成氏》和青铜铭文《幽公盨》为进一步了解上古大禹神话提供了新思路。
上古神話幸賴於上古文獻記載,方才傳至後世。我們現在研究上古神話同樣要依賴於這些上古文獻,否則我們就會落入“巧婦難爲無米之炊”的境地。由於時代久遠,相對於汗牛充棟的古代典籍來說,上古神話在文獻古籍中載錄甚少,因此,簡帛神話的吉光片羽都是彌足珍貴的,值得我們珍視。
(三)簡帛辭賦
辭賦是中土特有的文體,“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爲西方所無;又曾受君上的隆重恩寵,既“頌美”又“諷喻”,爲有些文體難以企及。簡帛辭賦主要有上博楚簡的四賦《李頌》《蘭賦》《有皇將起》《鶹鷅》、銀雀山漢簡《唐勒賦》、阜陽漢簡《楚辭》、尹灣漢簡《神烏賦》、北大漢簡《反淫》等。上博楚簡的四賦深具楚辭之風,托物言志,表現了楚人的自然性情。《唐勒賦》的出土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學史價值,解決了文學史上唐勒賦與宋玉賦是否存在的學術公案。“戰國時代會不會有散體賦形式的出現,曾是研究者判斷宋玉賦真僞問題的論據之一。唐勒賦的被發現,則對斷定今傳宋玉賦的真實性增加了有力的論據。”阜陽漢簡《楚辭》的出土意義重大,正如阜陽漢簡整理組所說:“阜陽漢簡《楚辭》雖說僅存下片文只字,但它是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2100多年前屈原作品的最早寫本。一字千金,十分可貴!”廖名春亦指出“屈原的作品是否系漢人僞託的間題隨著阜陽漢簡《離騷》、《涉江》殘片的出土可以說成定論了”。尹灣漢簡《神烏賦》面世把古代俗賦的起始時間提前了200多年,也爲漢代俗賦研究提供了難得的珍貴資料。北大漢簡《反淫》的出土,說明西漢時期枚乘的《七發》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也反映了西漢時期散體大賦的發展狀況。
簡帛辭賦豐富了辭賦研究的園地,開展此項專題研究可以彌補現有辭賦學術研究的不足,解決辭賦嚴重的一些疑難問題,拓寬辭賦研究的視野。
(四)簡帛散文
散文涵蓋面相對較寬。六朝以來,爲區別于韻文、駢文,而把凡是不押韻、不重排偶的散體文章,統稱散文。應該說,在古代文學作品中,散文所占的比例最大。簡牘散文包括以下幾類:(1)戰國楚簡散文,如《恒先》《彭祖》《三德》《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唐虞之道》《忠信之道》。(2)秦簡散文,如雲夢秦簡中的《語書》《爲吏之道》;(3)漢簡散文,如銀雀山漢簡中的《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晏子》。繒帛散文有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黃帝四經》《相馬經》等。簡帛散文記載了頗多歷史事件和人物言行,具有補充傳世文獻的作用,同樣也可以豐富歷史人物的思想和形象。簡帛散文與傳世散文在體裁上具有相通性,比如史傳體、論說體、書信體等。作爲論說體的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在論說中提到“吏有五善”、“吏有五失”,而在《語書》則從“良吏”“惡吏”兩方面論說,這正反兩方面論說,反映出秦國論說文的結構特點以及辯證的思維方式。考慮到玉石散文如侯馬盟書與溫縣盟書值得關注,現亦作簡略研究,然後附錄於後。簡帛散文具有與詩歌辭賦不同的語言特點,其押韻方式、韻部、固定用語、句式、俚語俗言等都有待於進行系統地研究和比較。
在簡帛文學文獻中,散文文獻出土量最多,不容小視。我們對於散文的文學研究,不但有利於完善上古文學史,而且可以幫助文學以外的其他學術領域解決許多學術問題。
(五)簡帛古小說
目前學界對“小說”概念雖然爭執不下,但是屬於“街談巷語,道聽塗說”的簡帛古小說都已經蘊含有小說元素,而且這些具有小說元素的作品,實爲後世小說之濫觴已毋容置疑,甚至可以說它們是後世小說的起源。
靈化小說反映的是世俗與神靈雜糅的狀態,具有巫術的色彩。這種巫術色彩正是中國文學早期的常見形態,如《山海經》中的靈禽異獸,“見之則天下……”,便可視之爲靈化因素。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乃早期靈化小說的代表,將它與其他作品中的靈化因素進行比較,就可以探討靈化小說在人物塑造、情節設計、藝術手法等方面的特點。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體現先秦時期一篇小說作品原貌,這在文學史上應當是一個重大發現,甚或是解開中國古代小說起源之謎的一把鑰匙。清華簡《耆夜》本身就是戰國時期小說家擅長寫作的一篇“小說”而已。我們倘若能夠正視《耆夜》的小說屬性,即從文學角度對其進行解讀,那麽我們對其爭論的許多問題可能就會迎刃而解,因爲這許多問題主要是由於“歷史文學化”造成的。放馬灘秦簡《墓主記》所具有的志怪因素已基本得到學界的認可。講的是一個名叫“丹”的人死而復活的過程。這種志怪故事,“反映了佛教輪回思想傳入以前人們對死後情形的宗教信仰”,是先民生死觀念的體現。它與魏晉時期流行的志怪小說在結構、過程、結局等方面均具有一定可比性,尤其是主人公死而復生的情節,更是後世小說中的常見情節。古代小說中常見男女愛情受阻導致女方自盡的情節模式,這一小說類型甚至可以上升爲一個母題,即貞女愛情悲劇母題。對簡帛文獻中的貞女愛情悲劇母題可以進行縱向和橫向雙向比較。以敦煌漢簡《韓朋故事》爲例,該殘簡大概主要是漢代用作講故事者的底本的,相關文獻記載有《搜神記》、敦煌寫本《韓朋賦》等,將這些相關記載集中到一起進行縱向比較,可以考察出該小說發展演變的軌迹。同時,將其他貞女愛情悲劇小說集中在一起,包括《說苑》中“敬君因畫失妻故事”、《孔雀東南飛》、《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載“華督悅孔父妻”等,從情節、人物、結局、思想等方面都可以總結出該類型小說的創作模式。另外,敦煌簡《田章傳說》、敦煌簡《韓朋故事》、北京大學漢簡《妄稽》等。敦煌簡《田章傳說》“內容與敦煌寫本句道興《搜神記》《晏子賦》《孔子項托相問書》等有關,對於研究漢、唐兩代的俗文學之間的密切關係具有重要的價值”。北京大學漢簡《妄稽》“記錄了一個士人家庭內部因妻妾矛盾而引發的故事,情節曲折,語言生動,文學性很強,應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篇幅最長的‘古小說’”。《妄稽》的發現證實了小說這種形式從戰國一直流傳至西漢,同時也說明西漢時代已存在相當成熟的世俗題材小說。
總而言之,簡帛文獻給文學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珍貴的出土資料可以彌補一些文學史研究中的一些缺環,可以令上古文學史面貌煥然一新。在我們仔細分析與研究簡帛文學文獻之後,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已有的文學看法可能就會受到衝擊,過去的文藝理論可能就會受到挑戰,由此帶來的就是我們對於早期文學史的重新思考與認識,增強了我們改寫或重寫上古文學史的信心。
第二節 簡帛文學研究背景及其意義
一、簡帛文學研究背景
簡帛文獻是簡帛文學存在的前提。隨著20世紀初簡帛文獻研究的展開,簡帛文學的概念才可能得以形成,簡帛文學的研究也才可能獲得有效進展。未來簡帛文獻的出土,亦將繼續爲簡帛文學研究提供廣闊的空間。然而,簡帛文學研究氛圍的形成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尚古”傳統爲簡帛文學的研究提供了文化價值的力量。在“尚古”這一學術傳統的影響下,古代的幾次文獻出土都爲當時的學者所關注。漢武帝時期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出簡牘,對經學今古文之爭影響深遠。晉初汲郡出土簡牘,對晉代學術風貌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如裘錫圭所言,“從歷史上看,我國學者自來都很注意利用考古發現的古抄本和其他古代文字資料來校讀傳世古籍”。正是“尚古”傳統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得歷代學者重視簡帛文獻,具有較強的利用簡帛文獻的學術意識。簡帛文學文獻是埋在地下沒有改動過的相對真實的文學資料,一經出土,便成爲文學史界關注的焦點,也必然會促進較薄文學的研究。
其次,“二重證據法”爲簡帛文學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論基礎。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這一方法不僅成爲古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更是簡帛文獻研究的指導理論,其言:“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爲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考古材料,並借助考古的最新成果進行簡帛文學的研究。
再次,簡帛文獻不斷湧現在客觀上爲簡帛文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研究材料。陳寅恪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簡帛文學文獻的出現,解決了文學史上衆多爭論不休的問題。例如,關於唐勒其人,《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曰:“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漢書•藝文志》著錄《唐勒賦》四篇,然其作品不見流傳,關於唐勒的事迹也十分簡略。1972年隨著銀雀山漢墓《唐勒賦》的出土,不僅對研究唐勒其人其辭意義重大,更爲宋玉賦公案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也補充了從屈原楚辭到漢賦轉變的關鍵環節——散體賦這種文學形式。學界對《晏子》《尉繚子》《六韜》《鶡冠子》等上古典籍真僞的原有質疑,在這些古籍出土之後也就釋解了。自20世紀70年代至今,簡帛文獻不斷出現,充實了上古文學研究的內容,爲許多上古文學現象找到了更爲合理的解釋,如此則較爲準確地勾勒出了上古文學發展的原貌。
最後,學界對簡帛文獻研究的多元化趨勢推動了簡帛文學的研究。上個世紀以來,簡帛文獻備受重視,相關研究如火如荼,考古學界、古文字學界、史學界、哲學界等都産生了許多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隨著新簡帛文獻的不斷整理和發佈,簡帛文學研究亦蔚然成風。學界發表了大量具有真知灼見的論文,如李學勤關於《墓主記》的研究、裘錫圭關於韓朋故事的研究、湯漳平關於屈原《遠遊》的研究以及大量的關於上博簡《孔子詩論》的研究,新出的文學史專著同樣增添了簡帛文學研究內容,如禇斌傑、譚家健主編的《先秦文學史》已經注意吸收了簡帛文獻的研究成果,傅璿琮、蔣寅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先秦兩漢卷》單列了“先秦兩漢文學與簡帛文獻”章節,趙逵夫的《先秦文學編年》則充分運用簡帛文獻和當代考古成果。值得一提的是,“簡帛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自1999年以來,在姚曉鷗、湯漳平、蔡先金等努力下已經成功舉辦了四屆。1999年12月,在姚曉鷗教授主持下,在北京廣播學院舉辦了第一屆,這是開創之舉;2008年12月,在湯漳平教授主持下,漳州師範學院主辦了第二屆,具有接續之功;2012年11月、2014年8月,在蔡先金教授主持下,在濟南大學分別召開了第三屆與第四屆,亦取得豐碩成果。當然,與其他學科相比,古代文學史界對簡帛文獻的重視與研究仍需努力。
在中國文學史上,簡帛文學是一個嶄新的概念,它以簡帛文學作品與簡帛文學參考文獻爲主要研究內容,旨在以簡帛文學文獻補充傳世文獻之不足,還原上古文學發展的較爲真實的面貌。受“尚古”傳統的影響,在“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依靠大量出土的上古文學文獻,順應簡帛文獻研究多元化趨勢,簡帛文學研究定將勢不可擋,最終成爲“預流”中的一股潮流。
二、簡帛文學研究意義
杜維明曾經在說到郭店楚簡時認爲“我們現在所見的楚簡資料只是冰山的一角,這些資料和死海所出的《聖經》的早期資料一樣重要,在很多地方可能更重要”。簡帛文獻對於中國古代文學史構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簡帛文獻資料較之其他傳世上古文獻資料相對更爲可靠,以此爲基礎可以更爲方便和準確地勾勒上古文學發展的原貌。大量上古簡帛文獻的問世,對重新認識與重新審視上古文學史提供了寶貴的證據與嶄新的視角。簡帛文學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對其開展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可以爲進一步充實上古文學史甚至重寫上古文學史提供理論依據和實際支撐材料,有助於勾勒出一種新型的上古文學史圖景;可以促使人們重新省視傳統文學文獻,有助於醇厚當前文學研究界的學風,從而有可能帶動傳統文學史研究領域的突破性進展。總之,積極利用簡帛文獻,是推進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途徑,尤其在現實狀況下就更值得我們的關注與探究了。
(一)簡帛文獻爲上古文學研究提供新材料
現有傳世文學史料存在一定的缺失與不足,簡帛文獻就爲文學史新證提供了可能性。歷史上由於兵燹、禁毀、自然災變以及典藏技術等原因造成古書籍亡佚慘重,流傳下來的不足十一,《漢書•藝文志》著錄古書13269卷,幸存傳世者僅115種(其中先秦60種,秦1種,漢54種)。《左傳》所記最後年代爲西元前467年,而《戰國策》所記開始的年代爲西元前334年,由於文獻的缺失,歷史記載出現了約133年的空白,這就出現包括文學史在內的歷史缺環。既然我們能夠看到的資料如此之少,那麽我們的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以偏概全”之疏忽。
古代文學史研究確實需要不斷地拓展新領域,方可帶來持續的學術活力,而運用新史料是其重要的途徑之一。文學史料是研究的基礎,新文學史料擴大了原有史料的範圍,如此帶來的不但研究範圍可能寬了,而且研究基礎也可能就更爲堅實了,考訂的成果質量可能就更爲可靠了。簡帛文獻面世爲古代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機遇,古代文學研究者當然不能熟視無睹或作壁上觀。文學史作爲大學課程和著作形式,上個世紀初由於引進西方新的學術範式才在中國出現,由起初的較爲粗陋到現今的較爲完善,經歷了不斷補充與修正的過程。但是,任何學科的發展都沒有終結的時候,尤其文學史學科發展又往往受到現有史料的制約。簡帛文獻的出現,既爲我們增添了新的文學史料,又可能令我們對史料的認識發生變化,結果可能足以改變文學史的現有面貌,如20世紀以來楚辭研究之所以出現空前繁榮之景象,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大批簡帛文獻的發現,從而將楚辭研究不斷引向深入。未來古代文學研究領域要取得突破性進展,無非主要依賴于兩條路經,要麽採用新的研究理論與方法,要麽期待著新材料的發現。因此,未來古代文學研究最好從這兩個方面用功,不可偏頗,方可取得意想不到的結果。
大批佚失的文學作品的重新發現,在文學史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補白作用。當文學史圍繞作品、世界、作者、讀者四大要素開展研究的時候,作品仍舊處於核心位置,沒有文學作品的存在,一切文學史皆爲枉然。敦煌文學文本的發現直接導致在中國文學研究中形成了一個敦煌文學的重要分支。大批早已佚失的文學作品的重新發現,不僅補充了了新的文學史料,甚至改變了我們對以往的文學史的認識。
簡帛文獻展示的文學世界是“尋找回來的世界”。所有文學藝術作品既是作者創作的,更爲重要的是當時“世界”背景下的産物。當簡帛文獻提供大量經濟社會、思想文化、藝術審美、民俗風情等多個方面材料的時候,我們就會更爲清楚地看到古代文學藝術孕育産生的背景及其呈現的世界圖景,從而深化我們的文學研究。當我們運用大量簡帛文獻提供的直接或間接的材料進行文學史考訂的時候,我們就是企圖在復原古代文學世界的真實面目,使現有的文學史研究更接近于當時文學的現實。由此看來,簡帛文獻確實可有助於重現被歷史掩埋的一些文學史現象。
簡帛文獻對於區域文學史以及文學傳播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世界有區域之差別則許有文化之差異,廣穀大川,五方之民,異風異俗,可謂常理,“蓋五方地氣,有寒暑燥濕之不齊,故民群之習尚,悉隨其風土爲轉移”。南北文學本有區別,上個世紀中期以來,楚地的考古發掘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前所未知的輝煌燦爛的楚文化世界,楚簡中的詩賦十分可觀,如銀雀山漢簡《唐勒賦》、上博簡《交交鳴烏》《蘭賦》,楚地文學史研究理所當然地被提到了議事日程,同時還可以更進一步研究南北文學文化交流與傳播情況,如從上博簡《孔子詩論》可以推斷南北詩學融合之趨勢。秦地文學文獻的出土,可以轉變人們對於原來認爲秦無文學的看法,並且可以發現秦文學的傳播情況,如從出土的《日書》文獻或可推斷牛郎織女傳說的源頭在秦地。
(二)簡帛文獻爲解決古代文學史上的學術公案提供了契機
所謂學術公案就是指在某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學術問題上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由於各方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一段時期之內沒有公認的定論。文學史上學術公案很多,不勝枚舉。簡帛文學研究可以幫助解決文學史上的一些學術公案。關於孔子是否刪詩的問題,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爲孔子刪詩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而且還爲“詩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間。孔子與《易》的關係也爲學術史上的疑案。宋人歐陽修懷疑《易傳》與孔子的關係。后来亦多有怀疑者,至现代錢穆、李靜池等人纷纷加入质疑者行列,当代陈鼓应等人甚至推断《易傳》为道家之文,断言“《易传》的哲学思想,是属于道家,而非儒家”。而馬王堆帛書《易傳》的出土再次证明孔子與《易傳》之關係。自從疑古學風在宋代興起,不少傳世的先秦子書被懷疑是後人的僞託之作。如今本《六韜》《晏子春秋》《尉繚子》,有人懷疑它們並非《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先秦著作,而是漢代以後的僞作。但在西漢早期的銀雀山墓出土了這些書的部分篇章,內容與今本基本相同,說明今本應該就是《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先秦古籍。今本《孔子家語》一書,世間多以爲系魏晉學者王肅僞造。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出土的《儒家者言》卻與《孔子家語》相合甚多,有的學者推定其爲《孔子家語》的祖本,從而可能洗脫《孔子家語》的“僞贋”惡名,並重新予以價值評估。很多人懷疑《莊子》雜篇並非戰國時期的作品。而阜陽漢簡就出現了《則陽》《讓王》《外物》諸篇文字。張家山漢簡也有《盜蹠》篇。它們都屬《莊子》雜篇,“這些發現證明《莊子》雜篇距莊子不遠,它們應該是戰國時期的作品。”《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又有“《齊孫子兵法》八十九篇(圖四卷)”。《吳孫子兵法》即傳世《孫子兵法》,《齊孫子兵法》世稱《孫臏兵法》。由於《孫臏兵法》失傳,它的存在曾長期受到質疑。也有人認爲《孫子兵法》爲孫臏所作。西漢早期銀雀山漢墓《吳孫子》和《齊孫子》同時出土,使上述懷疑之論不攻自破,從而改變了學界對於孫臏其人的看法,爲先秦子學研究或兵學研究撥開了一團迷霧。上博楚簡《采風曲目》的出土,既說明我國先秦時期音樂發展已經達到了極高的水準,又說明我國先秦時期的音樂文學發展達到了相當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宮廷音樂文學可謂蔚然成風。重要的是《采風曲目》的出土再次驗證了周代采詩制度相當完善、“詩三百”詩樂一體以及南北音樂文學交融之成說,爲《詩經》學案中的“采詩”說以及“詩入樂”說提供了有力的證據。關於宋玉賦,曾有學者認爲戰國時代不會有散體賦形式,從而懷疑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提到唐勒和景差賦,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出土了《唐勒賦》殘篇證明了《史記》《漢書》記載的真實性。梅本古文《尚書》的真僞問題一直是一個學術公案,有人不遺餘力地企圖爲此書翻案,甚至論證空乏疏闊者亦放言厚誣,清華簡《尹誥》(《鹹有一德》)說的出現,使僞古文《尚書》案終成定讞。綜上所述,簡帛文獻爲解決中國文史上長期聚訟不已的學術公案具有重要的價值,乃至不可替代。
(三)簡帛文獻糾正傳世文學文獻之謬誤
簡帛文獻有助於還原傳世文獻的原貌,糾正傳世文獻之謬誤。現在傳世文本往往是經過輾轉抄寫的,抄寫的過程中就有可能産生脫文、錯簡、衍文、錯字、別字等問題,甚至出現魯魚亥豕現象,亦不足爲奇。倘若抄寫者主觀臆斷,擅自刪改,甚至可能會出現郢書燕說之問題,那就更爲遠離原文本,亦不罕見。爲了避免流傳時的錯誤,儘量保持文本的原貌,人們對古籍做了大量的校勘、整理工作。然而,因所據之本最早的也不過宋代人刊刻,其與上古文學文本之原貌是否相合,並非容易確定之事。
簡帛文獻更接近於歷史的真實,其所依據的材料往往更充分、更可靠。其埋入地下時如同打上了歷史的封印,不曾受到扰动。如此一來,將簡帛文獻與傳世文獻相校勘,可以起到相互訂正的作用。《戰國策•齊策》中有“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的記載。長期以來,誤寫作“左師觸讋願見太后”。清代學者王念孫曾指出當從《史記》作“觸龍言”。這一錯誤,由馬王堆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得以糾正。《詩經•小雅·巧言》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經師不得其解,鄭玄訓“邛”爲病,訓“止”爲“職事”,后多從之。郭店楚簡《緇衣》引为“非其止之,共维王恭”,意为“臣事君,言其所不能”即“止”,“不辭其所能”即“恭”,此與鄭玄之訓則大相徑庭。《詩經•七月》“以介眉壽”,“介”字難以索解,而銅器銘文中多有“用眉壽”、“用祈亡(丐)眉壽”等語,則知道“介”應爲“亡”之借字,即祈求之意。
(四)簡帛文獻與傳世文學文獻互補與互證
簡帛文學文獻爲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證據,大大促進了相關領域的研究,其重要價值不言而喻。然而其本身也有各種複雜的情況。傳世文獻雖然可能存在流傳上之弊端,但其歷經大浪淘沙,亦有其自身的優點,如經過了反復校勘和整理。因此,簡帛文學文獻與傳世上古文學文獻的關係應該是互補互證的。
1.簡帛文學文獻與傳世上古文學文獻的互補
據《史記》記載,西漢前期黃老之學盛行,此學說是當時決定國家政治的主導思想,並對當時的社會生活、文學藝術産生了深遠的影響,當時人們的文學作品中就體現出很明顯的黃老之學的色彩,如賈誼的《鵩鳥賦》等。然而,由於傳世文獻的匱乏,這就給黃老學派的思想的研究帶來了困難,以至於學界長期無人問津,也令學界感到深深的遺憾。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四篇,後定名爲《黃帝四經》,學界確認其屬於黃老學派代表作,從而在黃老之學上彌補了傳世文獻的缺憾。
儒家思想的兩大開山鼻祖孔子和孟子在時間跨度上經歷了春秋到戰國的一百多年的時間,在這期間除了《論語》《孟子》以及相傳爲曾子和子思所作的《大學》《中庸》外,我們沒有見到這百餘年間其他任何關於儒家思想的論著。那麽這期間儒家思想是怎樣從孔子到孟子作爲完整的哲學系統流傳下來的,成爲儒家思想史上的空白區。1993年郭店戰國楚簡的出土徹底解決了這一問題,《窮達以時》《忠信之道》《性自命出》《唐虞之道》《魯穆公問子思》《成之聞之》《語叢》《六德》《五行》九篇儒家佚書的出土填補了這一空白。從儒家人性學說發展來說,孔子重在教化,而關於人性本身的論述卻是很少的,在《論語•陽貨》篇中提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人性論觀點。但是,孟子的人性本善理論是很系統完整的,如《孟子•告子上》雲:“測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測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又《孟子•公孫醜上》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測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党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這些關於人性論的論述如果說是孟子直接由孔子那裏發展而來是相當牽強的,但是郭店楚簡中的這些儒家佚書就恰恰出現在孔孟之間的銜接之處,也就有力證明了孟子的性善論學說即非孟子原創,也非直接因襲於孔子,而是作爲一個理論體系代代相傳而來。龐朴就曾在《古墓新知——漫讀郭店楚簡》中說:“楚簡在孔子的‘性相近’和孟子的性本善之間,提出了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性一心殊等等說法,爲《中庸》所謂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命題的出場,作了充分的思想鋪墊,也就補足了孔、孟之間所曾失落的理論之環。”這就反映出出土散文文獻具有填補思想史上空白的作用。
簡帛文學文獻蘊涵著傳世文獻中所未見的思想文化內涵。在信陽長台關、荊門郭店、長沙馬王堆、臨沂銀雀山、定縣八角廊等竹簡帛書中,發現了傳世文獻沒有的文本或思想內容。這些大量的早期文本,說明中國文學或思想文化在上古時期的風貌。從文學性上看,很多前所未見的佚篇有較大的文學價值,如馬王堆帛書《易之義》關於“龍”的描寫,富有文學色彩和韻味。簡帛文獻的研究亦多依據傳世上古文學文獻,因此二者具有互補的關係。
2.簡帛文學文獻與傳世上古文學文獻的互證
受傳統儒道傳世文獻的影響,我們一直堅信儒道兩家在“仁”、“義”、“聖”這些傳統儒家核心價值觀念上一直處於水火不相容的對立狀態。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對於儒道的對立關係就曾指出“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但是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簡中《老子》甲本中有“絕知棄辯,民得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爲棄作,民複孝慈。”這樣一簡,而今本傳世《老子》在第十九章裏記爲“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這樣幾字的差別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我們對於傳統道家思想的認識。《搜神記》中記載有韓朋夫婦的故事,1979年甘肅敦煌西北馬圈灣出土一枚有關韓朋故事的漢簡,證明漢代已經流傳該故事,同時說明《搜神記》對於韓鵬夫婦故事的記載亦淵源有自。上述舉例均體現了簡帛文學文獻與傳世上古文學文獻的互證關係。
第三節 簡帛文學研究方法及應注意的問題
在出土文學研究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注意理論思考與研究方法的創新,既要遵循文學研究的傳統,又要借鑒相關學科新的理論與方法;既要防止以後出材料去證前期文獻,又要防止不尊重傳世文獻價值的孤證;如此古代文學史新證研究方可更有力度、寬度、深度與高度。
一、綜合運用多種學科的研究方法
簡帛文學是上古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將其放在中國古代文學的歷史長河中,才能觀見其時代特徵;也只有重視簡帛文學作品的文學地位,才能理清中國古代文學真實的發展軌迹。簡帛文學文獻同時又屬於出土的上古文獻,因此對它的研究還必須運用文獻學、文字學、歷史學、民俗學、宗教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領域的理論與方法,尤其要利用考古學的相關成果。簡帛文獻助益古代文學研究領域新證方法的形成與發展。從王國維、於省吾迄今,新證方法已得到普遍認同。從當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文學考古”一詞的提出到其研究方向與研究內容的確定,人們就不難發現其系屬文學史新證學派,也就是說“文學考古”是文學史新證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考證文學方面,是運用考古資料還是通過簡帛文獻,其結果是殊途同歸的。文學考古與文學史新證一脈相承的研究方法有力地促進了古代文學的研究。只有把簡帛文學與簡帛文獻結合起來,運用考古發現的上古文字資料、實物資料,才能準確地釋讀上古文學作品、全面地把握上古文學的整體風貌。
在研究簡帛文學時,要根據簡帛文獻的性質採用相應的研究方法。根據文獻的流傳情況,簡帛文學文獻可分爲有傳世本、無傳世本兩個類別,我們對這兩類文獻要採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沒有傳世本的簡帛文學資料,屬於佚籍重現。對於無傳世本的佚籍,要在釋讀文字、解讀文本的基礎上理解其文本與思想。文字釋讀、文本解讀的過程需要古文字學、文獻學的知識,在此基礎之上分析文本內涵,進而借助學術史的知識予以合理的定位。與之不同,研究有傳世本的簡帛文學資料,重在比較簡帛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異同。關於傳世文獻與出土資料的關係,尤其是二者的相異之處,要辯證地看待。如馬王堆出土帛書《老子》、郭店出土楚簡《老子》與傳世本《老子》不論在次序、文字,還是思想上都有很大的不同,通過比較帛書本、簡本與傳世本的異同,能夠清晰地看到後世學者對《老子》進行加工、整理的痕迹。正是簡帛文獻的印證,讓我們可以重新審視傳世文學文獻的歷史流變。儘管傳世文獻在流傳中經過了改動,與簡帛文獻存在很多不同,但不能簡單地以簡帛文獻爲優,更不能輕易否定傳世文獻的歷史作用。如帛書《老子》雖然比傳世本古老,但多錯漏、衍誤,故並非善本。傳世文獻在流傳中對學術産生了根深蒂固的影響,文獻的校勘本身就帶著歷代學者的解讀,故而對待簡帛文獻要採取慎重的態度、運用客觀的研究方法,盡可能在傳世文獻已經形成的學術框架中進行對比研究。對於簡帛文學文獻的考察,要根據其不同的流傳情況採取不同的方法,給其以合理的文學史定位。
二、運用簡帛文獻應注意的問題
簡帛文獻爲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證據,大大促進了相關領域的研究,其重要價值不言而喻。然而其本身情況也較爲複雜,亦並非十全十美。這就關係到對於傳世文獻與簡帛文獻的立場與方法的問題。傳世文獻雖然有流傳上的弊病,但其在傳承過程中大多經過校勘和整理,也有其自身的優勢。因此,在積極利用簡帛文獻推進文學史新證時,我們也應注意一些不可回避的問題。
(一)甄別簡帛文獻的優劣與真僞
簡帛文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簡帛文獻未必就是當時最好的文本,當時記錄的內容未必就全可信,因此我們應該採取審慎的態度。1972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中記錄有關蘇秦的資料與《戰國策》《史記》的記載大相徑庭,蘇秦與張儀生存時段與傳世文獻記載時間不合,經過考證,還是傳世文獻記載較爲恰切。所以,“如果認爲凡是簡帛文獻的史料價值都高於傳世文獻,可以照單全收,或者遇到史事與傳世文獻相異或矛盾之處,即以簡帛文獻爲依歸,這都不是科學的態度。”再說,簡帛作僞古已有之,目前可以追溯到漢代,上個世紀以來,簡帛文獻造僞亦是觸目驚心。由於商人逐利,甲骨文、青銅器銘文造僞已成不言的事實。石刻文獻亦同樣存在造僞,如僞刻魏唐墓誌。1961年至1962年間,新疆博物館兩工作人員合謀,利用13世紀的舊文書(真文物)上書寫僞造的所謂唐代的《坎曼爾詩箋》,曾轟動一時,那時舉凡涉及唐詩、民族文學之典籍,幾乎無一不予以採納,甚至還曾入選中小學課本,可知造成影響之巨大。這件贋品産生極壞的影響就可想而知了。本世紀初浙江大學入藏漢簡遭受嚴重質疑,造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些僞造的簡帛文獻危害程度肯定超過已有的傳世文獻,很容易造成新的僞史,值得警惕。因此,我們對於簡帛文獻應該作去僞存真、考而後信的真功夫。
(二)防止過度闡釋簡帛文獻
出土文獻由於大多是古體字所書寫,這就需要隸定、整理與考訂功夫,可能由於某一個字釋讀不准,就有可能帶來很大的理解歧義。如郭店楚簡《老子》出土後,其中有“絕僞棄慮”四字,由於裘錫圭首次釋讀有誤,後又作更改,帶來很大影響。另外,有些出土文獻內容可能屬於古小說,而“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漢書·藝文志》)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可以將古小說之內容完全作爲史實來看待。實際上,我們有時還是有意無意地過度闡釋出土文獻,將其可能虛構的情節落定爲歷史史實。如清華簡《耆夜》無疑是戰國時期文獻,但是該文獻中記載的詩作未必真的就是武王等所作,其實,這與《穆天子傳》十分相似,其中穆天子與西王母所作詩歌皆爲小說家所擬造,不應該做過度闡釋的。簡帛文獻也存在著精華與糟粕混雜的情況,我們同樣需要採取汲其精華而去其糟粕之態度,利用簡帛文獻從事文學史研究,就不能局限于簡帛文獻一隅,而應該盡可能廣泛地搜集與整理簡帛文獻材料,並與傳世文獻進行比照參證,以逐步探討與揭示文學生成和發展的原生狀態。對待簡帛文獻科學的態度應該是將已有的紙上文獻同簡帛文獻密切結合,做到兩者互證,使之相互發明,從而産生新認識、新觀點。
(三)重視簡帛文學參考文獻
在研究簡帛文學時,不僅要關注簡帛文學作品,還要重視簡帛文學參考文獻,這是由上古文學的特點決定的。上古時期,詩樂舞一體,文史哲合一。詩歌是詩文與樂歌相合而成,原始的詩歌以聲樂傳意,詩歌中的聲樂重于詩文,詩文依賴聲樂而存在。先秦時期的詩歌處在詩樂既相分相離、又相合相連的狀態中。上博戰國楚簡《孔子詩論》之“詩亡(無)隱志,樂亡(無)隱情,文亡(無)隱言”的思想,很好地展現了詩、樂尚未分離而又有所區分的狀態。《離騷》之詩樂相分,《九歌》之詩樂結合,也說明了這一文學史現象。時至漢代,詩樂亦沒有完全分離,樂府詩歌即配樂而歌。上古文學中文史難分,許多上古文獻兼有文學、史學的性質,如《左傳》《戰國策》,既是史學著作,又是文學散文。魯迅就曾經評價《史記》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因爲上古文學詩樂一體、文史不分的特點,使得上古文學的內容較爲廣泛,各類出土資料皆可能與上古文學息息相關。倘若說簡帛文學作品是研究簡帛文學的直接資料的話,那麽簡帛文學參考文獻就是研究簡帛文學的間接資料。非文字的出土資料,諸如春秋樂器、楚帛圖、漢畫像石等考古實物,對於研究上古文學同樣有著重要的價值。正如陳直所言,“自1940年長沙戰國時墓葬陸續被盜,後經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之正式發掘,所出銅、玉、漆、陶、竹、木各器,其花紋、繪畫、雕刻,無不精致絕倫。……楚國文物,燦然大備。知楚國由於經濟之發展,反映出文化之高度成就,與屈原之作品,有相互聯帶不可分割之關係。”銅、玉、漆、陶、竹、木等出土文物,雖與文學作品沒有直接的關係,卻能反映出文學家所處的時代背景,這是研究文學作品的重要輔助材料。因此,研究簡帛文學既要借助于簡帛文學作品文獻,同時還要充分利用簡帛文學參考文獻。
埋藏於地下的上古時期的文學文獻大量出土,推動了簡帛文學概念的形成。從簡帛文學文獻的字裏行間,已然可以感受到上古文學之風,但是要系統歸納簡帛文學的特徵,則必須採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只有將簡帛文學作品文獻與簡帛文學參考文獻結合起來,在廣闊的學術視野中借鑒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並區分有傳世本的文獻與無傳世本的文獻,才能在準確解讀文獻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無論是簡帛文獻還是傳世文獻,都是華夏民族的精神文化産品,繼承和開發這些珍貴的民族遺産,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也是我們當下應盡的義務和責任。
编辑:赵露晴 初审:刘雯 复审:俞林波 终审:张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