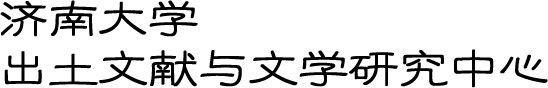绪 论
20世纪以来先后出土的简牍文献资料,如甘肃武威汉简、安徽阜阳汉简、河北定县汉墓竹简、郭店楚墓竹简、连云港尹湾汉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不仅对于考索古代风俗、礼制,丰富中国古代哲学与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资料价值,其中包含的丰富文学成分,还为上古文学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推进,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契机。这些简牍文献资料中的诗学部分,更为诗学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许多聚讼纷纭的论题由此得到新的认识。简牍文献中的诗学研究,事实上成为近期学术热点之一。这项研究虽然时间不长,但正如王国维所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新材料的发现大大开拓了诗学研究的视野。
第一节 简牍文献的诗学研究价值
《说文解字》云:“简,牒也,从竹间声。”又:“牍,书版也,从片卖声。”简牍是造纸术出现以前主要的文献载体,书之于竹称为“简”,记之于木谓之“牍”。简牍文献,指的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以竹简和木牍作为载体的文献资料。
在中国古代,纸未发明之前,竹片和木板曾是主要的书写材料。据林剑鸣《简牍概述》一书研究推测,简牍的使用最晚应该是在殷商时代,然而现在所发现的简牍文献其年代主要是从战国到东汉末年,即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2世纪。从东汉起,纸质书写材料逐渐取代了简牍,但简牍的书写应用大概一直持续到公元4世纪,之后才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中国使用简牍书写的历史长达一千多年。
简牍文献,作为重要的地下材料,或可补史籍之缺,或可正史载之讹误,甚至将改写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简牍文献中关于诗学的部分,对上古诗学研究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计的。
简牍文献资料,不但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关于诗学的佚书,也提供了一些目前尚有传本的古书的早期本子,这些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先秦以及汉代诗学问题的认识。郭店简和上博简中都有《缁衣》篇,在传世文献《礼记》中也有《缁衣》篇,将传世本《缁衣》与古本《缁衣》中引诗情况相对照,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些诗学研究的新问题。出土简牍文献中,佚书数量众多,有些佚书则是时代最早的诗学著作。上博简《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体系严密、结构完整的诗论著作,它运用哲学思辨的评论术语,阐释有关诗篇的主旨,成功构建起先秦诗论的基本理论框架,标志着我国的诗学评论在当时已逐渐进入自觉状态,在诗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上博简《采风曲目》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唯一一篇歌诗类作品,它明确记载了先秦时期的歌诗曲目和曲调,揭示了先秦用于演奏诗乐的文本形态,对研究当时的采风之制及其详情、先秦《诗》与乐的关系等有着重要的价值,对于解决一些《诗经》学史的问题也有帮助。阜阳汉简《诗经》是目前所知的最早《诗经》抄本,它的发现为《诗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字材料。《诗经》自问世以后,经秦火后至汉代复得流传。据专家考证,阜阳汉简《诗经》既非《毛诗》系统,也不属于另外三家《诗》中任何一家,至于属于哪一家我们姑且不论,但至少可以肯定汉代传《诗》者,绝非仅有四家,应该还有别家。因此阜阳汉简《诗经》足可以补文献之阙疑和不足。此外,阜阳汉简《诗经》中还发现《诗序》的残文,否定了只有《毛诗》才有《诗序》的传统观点,为《诗序》并非《毛诗》所独有,提供了新的、有力的佐证,因此,阜《诗》对诗学研究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清华简中四首乐诗,除了《蟋蟀》外,其他三首前所未见,其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方法
近以来,简牍文献中的诗学文献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截至目前,相关研究多局限在某些侧面,进行全面研究的文章或专著相对较少。这给本课题的展开带来了诸多困难,也为我们的深入研究留下了广阔空间。
一、研究现状
(一)郭店楚简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后经彭浩、刘祖信等编联、撰写释文与注释,由裘锡圭对书稿进行审定,于199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郭店楚墓竹简》一书,郭店楚简正式公诸于世。其中与诗学相关的篇章有《缁衣》《五行》《唐虞之道》《性自命出》《语丛一》《语丛三》等。此后,在美国召开第一次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研究郭店楚简的热潮。
对郭店楚简中诗学的研究,学者多关注具体诗篇或诗句的考释。薛元泽《郭店楚简〈五行〉“淑人君子,其仪一也”之解释——兼释诗经〈摽有梅〉〈唐风‧无衣〉〈鸤鸠〉》一文,主要对“淑人君子,其仪一也”诗句字词进行解释,并考释《摽有梅》《唐风‧无衣》《鸤鸠》三首诗篇的主旨。薛元泽还发表了《由郭店楚简〈五行〉“叔女”解〈诗经·关雎〉》、《郭店楚简〈五行〉相关诗句“不竞不絿,不刚不柔”之解》等文章。
考察先秦儒家对《诗》义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也是学者研究郭店楚简诗学的一个重点。杨朝明《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一文,从楚简论《诗》的材料,考察思孟之儒对《诗》义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认为子思学派继承了孔子的《诗》论特征。此类文章还有饶宗颐《诗言志再辨——以郭店楚简资料为中心》、廖名春《郭店楚简引〈诗〉论〈诗〉考》等等。
目前学界对郭店楚简的研究倾向于文字考释以及具体诗篇的解释,研究方向尚有待于丰富,研究范围亦有待于拓展。
(二)上博简
上博简最早发现于香港的文物市场,于1994年入藏上海博物馆。这批竹简数量庞大,经过专家的不懈努力,基本完成了竹简的整理与考释,从2001年到2008年分册出版,共出版七册,其中与诗学相关的有《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民之父母》《采风曲目》《逸诗》《曹沫之陈》等。
上博简陆续公诸于世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有关上博简中诗学研究的文章和专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对简文字词方面的考释仍是研究的重点。如王宁《逸诗〈交交鸣乌〉笺释》、刘乐贤《楚简〈逸诗·多薪〉补释一则》、季旭昇《〈上博四·逸诗·交交鸣乌〉补释》季旭昇《〈采风曲目〉释读》、黄鸣《上博四〈采风曲目〉零拾》、陈思婷《试读上博(四)·采风曲目“苟吾君毋死”》等,都是这方面的成果。
对简文的作者以及创作时代的研究,也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如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陈立《〈孔子诗论〉的作者与时代》,对《孔子诗论》的作者以及创作时代进行探究。秦桦林《楚简佚诗〈交交鸣乌〉札记》一文,考证逸诗《交交鸣乌》为战国儒者的模拟之作。陈文革《解读战国楚简〈采风曲目〉》认为,《采风曲目》中的乐曲为南方传统的民歌,并从音乐学角度对乐曲和音名进行分析。
此外,学者对竹简的简序编联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如濮茅左《〈孔子诗论〉简序解析》、饶宗颐《竹书〈诗序〉小笺》等,都是从简序编联方面对《孔子诗论》进行研究。
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一书,将战国诗学分为南北两派,并认为《孔子诗论》填补了先秦零散的《诗》学评论到汉代四家诗成熟《诗》学之间的空白,开辟了诗学研究领域的新境界。
但总体而言,学术界对上博简中诗学的研究仅仅局限在一两个方面,多关注文字及作者考释、简文编联等方面,上博简的诗学价值仍有待进一步的挖掘。
(三)阜阳汉简
1977年,安徽省阜阳双古堆出土汉简《诗经》残卷,此后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胡平生、韩自强发表《阜阳汉简〈诗经〉简论》一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一书,将阜阳汉简《诗经》与今本《诗经》以及已经亡佚的齐、鲁、韩三家《诗》进行了认真的比勘,认为它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诗》中任何一家的传本,“是否与《元王诗》有关也无从考证”,因此“推想它可能是未被《汉志》著录而流传于民间的另外一家”。
阜《诗》中异文考辨研究卓有成果,如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陆锡兴《〈诗经〉异文研究》,黄宏信《阜阳汉简〈诗经〉异文研究》等。
目前对阜《诗》的研究多集中异文考辨、阜《诗》与四家《诗》的对照比较上,而对阜《诗》中诗学价值的其他方面研究甚少,有待于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四)清华简
清华简是2008年7月由清华大学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竹简的年代考定为战国中晚期。内容大多为前所未见的经、史类书,其中与诗学研究相关的主要是《耆夜》。这部分简文目前公布尚少,且残缺较甚,因此论者较少。
对清华简《耆夜》中四首乐诗的研究,目前多集中在诗篇《蟋蟀》的释读上。如李学勤《清华简〈耆夜〉》一文,披露了清华简《耆夜》绝大部分简文,并提出简文《蟋蟀》为后世《唐风·蟋蟀》的祖本,孙飞燕《〈蟋蟀〉释读》一文,与此观点一致。刘成群《清华简〈旨阝夜·蟋蟀〉献疑》,认为《蟋蟀》“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且简文将作者定为周公应该是战国之人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手法。
清华简中四首乐诗,除《蟋蟀》外,其他三首诗篇的诗学价值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虽然《蟋蟀》已有学者进行释读,但是研究的层面有待深入。因此,清华简中诗学研究的空间较大。
如上所述,简牍文献中的诗学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但是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多倾向于简文的释读和考辨,研究方向、研究范围尚有待于拓展。首先,逸诗这一概念还需要认真细致的界定,对于其产生的原因亦应深入探讨;第二,关于简牍文献中的诗学研究,已有的成果大都从一个角度进行,比较零散琐碎。同时已有的一些看法,也往往是点到为止,缺少进一步的分析阐释;第三,有些诗学问题,如清华简《耆夜》中除《蟋蟀》外的三首古诗,尚未引起重视。
笔者试图在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简牍文献中的诗学资料的宏观掌握,对已有的论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恳请方家是正。
二、研究方法
采用“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为中心,对照相关传世文献,运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来探究简牍文献在诗学研究方面的价值。同时,立足于国内外学术界诗学研究现状,广泛吸收学界简牍文献的诗学研究的新成果,力求言必有据,避免凭空说话,在把握、解读简文的基础上,佐以传世文献资料,以期对简牍文献中的诗学部分有一个全面的关照,对先秦诗学的整体风貌和水平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识和评述。
出土文献的研究现已成为国际、国内学术研究的一大热潮。笔者试图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简牍文献中的诗学资料的梳理与分析,对一些诗学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本论文涉及到简牍文献中引诗、逸诗、论诗等各个方面,由于笔者才疏学浅,能力有限,疏漏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望方家指正。
第一章 简牍文献中的“逸诗”
先秦时期,在《诗》三百篇之外,尚有一些诗歌流传,并为时人所称引,散见于《左传》《国语》《战国策》或《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先秦典籍中,它们或存诗篇名,或存诗句,或诗篇名、诗句并存,但并未被收录在《诗经》之中,学界习惯将这些诗之篇、章或者诗句统称为逸诗。例如《论语·八侑》引诗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前两句见于《卫风·硕人》,最后一句在今本《诗经》中无可考,疑为逸诗。先秦逸诗研究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但由于历代统治者对《诗经》的高度推崇,使得先秦逸诗的研究一直处在《诗经》研究的阴影之下。涉及到逸诗研究的著作,从宋代王应麟《诗考》、欧阳修《诗本义》,到清代严虞惇《陔余丛考》、郝懿行《诗经拾遗》、马国翰《目耕帖》、魏源《诗古微》以及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傅道彬《〈诗〉外诗论笺》等,从表面数量上看似乎对于逸诗研究的著作已有不少,但实际上这些研究仅仅是用著作中的一章、一节甚至是一段话,且关注点大都在逸诗辑佚上,这也使逸诗研究存在很大的空间,如逸诗范畴的科学界定,逸诗本身的诗学价值,逸诗产生的原因等。自上博简《逸诗》、清华简《耆夜》乐诗相继公布后,逸诗的研究更进一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第一节 关于“逸诗”
一、“逸诗”概念界定
逸诗概念界定,是逸诗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从传世文献来看,最早明确指出某首诗为逸诗的是汉代学者高诱,他在《战国策》《吕氏春秋》的注释中,对文中引《诗》的情况曾作出过注释,并说到:“出自《诗经》某某篇”、“逸诗也”或者“逸诗篇名也”。但较长时期以来,逸诗概念一直没有得到很恰当的表述。其中,最早对逸诗下定义的是宋代经学研究者郑樵。
(仲尼)得诗而得声者三百篇,则系于风雅颂,得诗不得声者,则置之,谓之逸诗。
郑樵对逸诗概念的认识是以“孔子删诗”为中心,以诗篇“是否得诗得声”为标准的,这显然是片面的。
今人曹茂良曾撰文探讨逸诗,认为:
20世纪以来曹茂良曾发表文章《先秦逸诗初探》,将逸诗概念理解为:
其中既有黄帝弹歌、伯夷薇歌、琴操歌谣词曲,又有“鲁卫齐晋郑宋吴赵成徐秦楚、君臣民庶妇女胥靡优杂歌讴操曲诵祝相曲”“谚古语古言鄙语野语俗语故语民语不恭之语”等等,不一而足。
他将逸诗与民谚、民谣、野语等并列为同一概念,这显然是不恰当的认识。之后,赵逵夫在《先秦佚诗与先秦诗歌的发展》一文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诗经》、《楚辞》之外,见于各种文献的先秦歌谣、诵、辞之类300余首。
将先秦歌谣、诵、辞之类的先秦诗歌统归为先秦佚诗,扩大了逸诗的范围。此后,周秉高在其《论先秦逸诗》一文中,也对先秦逸诗概念进行论述:
风骚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面旗帜、两杆高标;而除此之外,先秦还有大量其他诗歌,其包括后代典籍辑录的少量上古歌谣和先秦历史散文、诸子散文、汉代史书或其他典籍中记载的相当数量的歌谣辞诗,不妨统称之为“先秦逸诗”。
他将上古的歌谣、先秦与汉代典籍记载的歌谣与辞诗,统称为先秦逸诗。这些歌谣辞诗虽然都有韵律,但其与逸诗是不能混淆的概念。
总之,前辈学者们对逸诗的认识不同,但其共同的特点是,将逸诗与先秦歌谣、民谚、辞诗等概念划归为同义词,认为逸诗等同于《诗经》《楚辞》之外的韵语,这显然是不确切的。笔者不敢苟同。
逸诗概念中,“诗”是指《诗》文本,而“逸”正是相对于《诗》文本中的诗而言的,傅道彬在《〈诗〉外诗论笺》中也曾指出“所谓逸诗是相对于《诗经》的选辑编排而言的”。逸诗诗作时间我们不能给以确切的时间限定,但不应该超出殷商至战国时代。据此,笔者认为,逸诗是指在殷商至战国时代产生的一些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被引用过,而未见于今本《诗经》中的诗之篇、章、句。
二、逸诗产生原因探析
关于逸诗产生的原因,先贤早有论述,试举几例,以期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和探讨。
欧阳修在《诗本义》一书中,对逸诗产生原因以及数量进行了论述:
司马迁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郑学之徒皆以迁说之谬,言古诗虽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迁说然也。何以知之?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焉,以图推之,首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君,由是言
之,何啻乎三千。
他认为逸诗的产生原因即是孔子在删订三千篇古诗的过程中,淘汰掉的诗篇而形成的,将逸诗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孔子删诗。“诗三百”在孔子之前已经编订形成,这在目前学界几近公论。故此,欧阳修对逸诗的认识显然是片面的肤浅的。
其后,郑樵在《六经奥论·逸诗辨》中谈到:
《驺虞》《狸首》《采蘩》《采蘋》,古之乐节也,日用之间不可阙,今《狸首》亡,逸诗自逸,非夫子逸之也,观《狸首》诗可见矣。
又《六经奥论·删诗辨》:
删诗之说与《春秋》始隐、终获麟之事,皆汉儒倡之也。大抵得其乡声则存,不得其声则不存也。
他的观点非常明确,即反对孔子删诗导致逸诗产生的观点,而认为逸诗是在诗篇长期流传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并非借助人为删诗的力量。
明代李先芳在《读诗私记》一书中说:
如作诗之人可考,其意可寻,则录之,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寻,则删之。
他认为逸诗产生的原因依然是孔子删诗,然而删诗的标准产生了变化,不再是传统上的“思无邪”,而是以诗篇的作者是否可考以及创作诗篇的意图是否明白作为新的参考标准,以此决定此诗篇是否可以收录。
明代张次仲在《待轩诗记》中写道:
诗之见录者,必其序说之明白而意旨之可考者也,其逸而不录者,必其序说之失传,旨意之难考而不欲臆说者也。
他认为逸诗形成的原因是由于诗序的失传,而导致诗意难以考辨,因此不被收录进《诗》三百。这是对逸诗产生原因提出的新见解。
在前辈学者逸诗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关于逸诗的记载,拙文认为,逸诗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部分逸诗为殷商时代或者战国时代的作品;《诗经》收录的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歌,而殷商时代和战国时代的诗歌,是产生于非诗时代的作品,因此,未被收入《诗》文本之中。例如上博简中的两首逸诗,《交交鸣乌》《多薪》,极有可能是战国时代儒者的模拟之作,它们虽然未被收录《诗》三百之中,却在文化传承与集成的大环境下流传下来,成为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诗篇。
其次,漏收入《诗》文本之中;有些逸诗,虽然产生于《诗》文本编订的时代,但由于不符合采风之制的具体标准,或者仅仅就是采风之时漏掉的,因此,未被收录进《诗》三百。
《诗》文本的编订存在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各诸侯国太师收集整理本地诗歌,并经过加工,配上符合本地风格的乐谱,然后送交有筛选整理诗歌任务的周太师。如《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周太师按照一定的标准,最后完成《诗》文本的编辑,正如《荀子·王制·序官》云:“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讲的就是周太师编选诗歌的情况。各诸侯国太师收集整理诗歌和周太师筛选整理诗歌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从西周初一直持续到春秋中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各诸侯国太师和周太师在编辑诗歌的时候,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些诗歌被删掉,但这些诗歌有的依旧在当地流传,并被学者士大夫称引且记录下来,就成为漏收入《诗》文本之中的逸诗。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诸侯国编辑整理的本地诗歌,周太师并未采纳,因此,也成为漏收入《诗》文本的逸诗。楚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楚国是一个诗歌繁荣的国度,但“诗无楚风”在目前学界几近公论。这是由于采风之时楚国与周王朝之间政治对立、民族歧视等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楚歌”所用的楚乐体系与周王朝雅乐体系存在明显的差异,使其不符合周王朝采风之制,故这些曲目未被收入《诗》文本之中。例如上博简《采风曲目》中出现的众多先秦曲目名,除《硕人》外,其余皆未见于今本《诗经》。笔者认为,《采风曲目》记载的为“楚风”曲目,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原因,故未被收入《诗》文本中,但仍然在其诸侯国内流传。
第三,一次次修订《诗》文本。《诗》文本不是通过一时或某一人的编订而成,而是经过不同人的共同努力,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书的。吕绍刚、蔡先金认为:“《诗》的结集是一个动态过程。自诗产生时起,就有诗之记录,记录多了,就有了诗集,有了诗集,就有了文本之说。《诗》之文本在历史上可分为四种主要存在形态:一为‘康王’文本形态;二为‘前孔子’文本形态;三为‘孔子’文本形态;四为‘汉代’文本形态,‘毛传’文本为其代表。”在春秋前期,《诗》没有形成固定的传本,这期间确实有部分诗歌是收录在《诗》文本之中的,但由于传本的不固定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有些诗歌从《诗》的传本中逸出,而成为逸诗。此后,在传承过程中,《诗》文本一次次结集和修订,最后形成固定的传本,不过,一段时期内《诗》文本的最后修订本和以前未修订本同时流传,旧本中被新本删掉的诗篇,有的被学者士大夫称引或者记录下来,在《诗》文本之外依然流传,便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逸诗。因此,《诗》文本的结集与修订在文化的连续性与传承性的大环境下,形成了今本《毛诗》之外的诗篇,也就是逸诗。这也是逸诗形成的主要原因。今人袁长江在其《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一书中,对逸诗的产生也有相关的论述。他认为:“逸诗的出现有两种情况:其一,民间的诗歌创作出来之后,只是被人们口头传唱。……后来被某些士大夫学会,在某种场合应用,又被用文字记载下来,不过这种情况较少。其二,逸诗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一次次的修订本《诗经》的出现。”他所讲的第一点原因,可以说是不多见的偶然的,不具有代表性。但第二个原因是逸诗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节 上博简中逸诗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中《逸诗》和《采风曲目》,是极富价值的先秦诗学文献资料。其中简文中的两首逸诗《交交鸣乌》《多薪》为后世文献所未见,对先秦逸诗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采风曲目》作为战国时期编辑的乐曲文本,其记载的曲目除《硕人》外,其余皆不见于先秦文献记载,它对我们研究考定战国时期《诗》与乐的关系以及当时“采风”之制与详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逸诗》
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战国竹简残卷中整理出两篇逸诗,为后世文献所未见。原简中并无篇名,整理者分别以诗章首句、诗意名篇,定名为《交交鸣乌》《多薪》。
(一)《交交鸣乌》
针对上博简中的《逸诗》,马承源先生曾作《〈逸诗〉释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出版之后,许多学者在马文的基础上作了很多新的考释和训解,季旭昇的《〈博四·逸诗·交交鸣乌〉补释》、廖名春的《楚简〈逸诗·交交鸣乌〉补释》等,都是此类。季旭昇还有《〈交交鸣乌〉新诠》一文,考证该诗是楚国贵族赞美楚王的诗篇,并将其归为《楚颂》,而赞美的对象以楚庄王的可能性最大。学者对《交交鸣乌》的研究考释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使此篇逸诗基本得以读通,然其中仍有诸多问题无法解决,目前只能存疑。
按照残简诗篇的章句序列统计,《交交鸣乌》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同时通过各章之间有几句完全相同或者仅有个别字不同的特点,可以在相互比较中补出其残缺的文字。现将《交交鸣乌》抄录如下:
交交鸣乌,集于中梁。恺俤君子,若玉若英。君子相好,以自为长。恺豫是好?惟心是向。间关谋怡,偕芋偕英。
交交鸣乌,集于中渚。恺俤君子,若豹若虎。君子相好,以自为武。恺豫是好?惟心是藇。间关谋怡,偕上偕下。
交交鸣乌,集于中澫。恺俤君子,若珠若贝。君子相好,以自为慧。恺豫是好?惟心是励。间关谋怡,偕少偕大。
这首诗以“乌”起兴,从品德、仪表、才华三个方面来赞美君子美好的品性,能够使人际关系较为和谐。
关于“乌”字,李零、季旭昇释为“乌”,意为“乌鸦”。在《诗经》中涉及到“乌”的诗篇诗句有:《邶风·北风》:“莫赤匪狐。莫黑匪乌”;《小雅·正月》:“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这两首诗中的“乌”为孝鸟乌鸦,而用“乌”来比喻君子的美好品行在《诗经》中未见。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载,有一种水鸟,是河乌科中的褐河乌,“褐河乌通体几乎纯黑褐色……栖息于山谷溪流间,多成对活动,也见于大江沿岸……能在水中游泳和潜水。”文章认为,“乌”应该是南方的一种水鸟。秦桦林也在《楚简佚诗〈交交鸣乌〉札记》一文中,通过诗句“集于中梁”“集于中渚”“集于中澫”推断,“乌”并非《诗经》中所描述的常见的乌鸦,而是一种栖息在水滨且善于鸣叫的鸟类。
从诗篇的韵部上看,第一章押阳部韵(梁、英、长、向);第二章押鱼部韵(乌、渚、虎、武、藇、下);第三章押月部韵(澫、贝、慧、励、大)。第一章和第三章都是隔句押韵的句尾韵,第二章为首句入韵而后隔句押韵的句尾韵。因此,这首诗符合《毛诗》的用韵,韵律工整精准。
从语言方面看,《交交鸣乌》用词典雅,诸如“若玉若英”“若珠若贝”“君子相好”“偕芋偕英”等,字词高雅,正所谓是阳春白雪。
从诗篇格式上看,首先,《交交鸣乌》采用《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并运用重章叠句的表现手法;其次,运用《毛诗》的譬喻,以“乌”起兴,比喻君子的美好品性;第三,在语法结构,每章前四句,都与今本《毛诗》相类似,例如:
“交交鸣乌” “雝雝鸣雁”(《秦风·匏有苦叶》)
“交交黄鸟”(《秦风·黄鸟》)
“集于中梁” “集于中泽”(《小雅·鸿雁》)
“集于灌木”(《周南·葛覃》)
“集于苞栩”(《唐风·鸨羽》)
“恺俤君子” “岂弟君子”(《大雅·旱麓》)
“岂弟君子”(《大雅·卷阿》)
“岂弟君子”(《小雅·青蝇》)
“若玉若英”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卫风·淇奥》)
然而每章从第五句“君子相好”之后的诗句,都与今本《毛诗》结构有差异。
综合以上几点,笔者认为《交交鸣乌》在许多方面与今本《诗经》中的作品相一致,诗歌的结构形式也很相近,重章叠句,复沓回环;手法相同,以鸟鸣之音,引出所要歌咏之事。简本应该为战国时代楚国贵族创作的楚歌,并受到《雅》诗的影响。马承源《〈逸诗〉释文》认为,这两首逸诗是采风之后经过修饰的,但并未收录,成为采风之后的孑遗之作。两首逸诗既然经过修饰,为何每章的前四句与今本《毛诗》相似,而后四句却差异较大,因此,将这两首逸诗考定为采风之后孑遗的观点有待商榷。
(二)《多薪》
简诗《多薪》有较多的残缺,现存的仅仅是此诗其中两章的部分诗句,共计四十四个字,重文八字。在马承源《释文》的基础上,廖名春的《楚简〈逸诗·多薪〉补释》对其拾遗补阙,考释了竹书《多薪》简一的疑难问题,补释了简二的残缺文字,同时对诗中的比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进一步提出《多薪》为楚地之作。季旭昇《上博四零拾》、董姗《读〈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四)杂记〉》、陈思鹏的《初读上博竹书(四)文字小记》、李锐的《读上博四札记(一)》以及杨泽生《读〈上博四〉札记》等等,都是对《逸诗·多薪》的研究,然多为字句的考释。现将《多薪》“释文”抄录如下:
……兄及弟淇,鲜我二人。
多薪多薪,莫如雚苇。多人多人,莫如兄弟。
多薪多薪,莫如萧荓。多人多人,莫如同生。
多薪多薪,莫如松梓。多人多人,莫如同父母。
《多薪》一诗主旨明确,即歌颂兄弟之间亲密的关系。诗歌以“薪”起兴,用“薪”来突出强调雚苇、萧荓、松梓之美好,从而对比起兴兄弟亲情与一般友情之关系。我们知道,在《诗经》中“薪”这一词多次出现,例如:
《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
《齐风·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
《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
《陈风·扬之水》:“扬之水,不流束薪。”
《豳风·东山》:“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小雅·大东》:“有冽氿泉,无侵获薪。”
《小雅·车舝》:“陟彼高冈,析其柞薪。”
《小雅·小弁》:“伐木掎矣,析薪扡矣。”
“薪”在先秦时代是重要的婚姻聘礼。宋段昌武《毛诗集解》引陈氏说:“析薪者,以兴婚姻。”又载曹氏说:“诗人常以婚娶比析薪,欲析薪者必之髙冈,欲娶妻者必求大国,高冈之柞必伟,大国之女多贤……故诗人之托意如此。”《诗经》中的“薪”“不仅显示其作为聘礼的功能,更多的是由此引发出更多的相关的喻义,如以析薪伐薪来表达性爱,比喻求偶;以束薪代表妻室,比喻男女和合与夫妻关系牢固等,从而成为婚爱的隐喻。”古代诗人取兴经常用“薪”,且“薪”更多的是婚爱的美好象征,而逸诗《多薪》中用“薪”来烘托突出其他事物的美好的这种写法并不多见。正如廖名春所说:“与《诗经》比较,《多薪》诗的比兴又颇有不同”,两者虽然都是用“薪”起兴,但所比兴的内容并不同。
从诗篇的句式上,《多薪》中所用的句式为(残缺的诗章不包括在内):
多薪多薪,莫如A1。多人多人,莫如B1。
多薪多薪,莫如A2。多人多人,莫如B2。
多薪多薪,莫如A3。多人多人,莫如B3。
诗篇句式为典型的重章叠句,且每章仅仅更换两个名词。在《诗经》中可以见到与之相类似的句式有:
硕鼠硕鼠,……,莫我A1。……
硕鼠硕鼠,……,莫我A2。……
硕鼠硕鼠,……,莫我A3。……(《魏风·硕鼠》)
在《诗经·小雅·常棣》中也有“莫如兄弟”句式: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诗经·小雅·常棣》)
在《诗经》中,《魏风·硕鼠》《小雅·常棣》的句式和《多薪》的句式相类似,但未见与其完全相同的句式。
从诗篇的韵部上,《多薪》第一章押微、脂部(苇、弟),微、脂通韵;第二章押耕部(荓、生);第三章押之部(梓、母)。且每一章中薪、人押真部韵。《诗经》中的押韵规律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隔句押韵的句尾韵;一种是首句入韵而后隔句押韵的句尾韵。因此,《多薪》的韵部与《诗经》的押韵规律存在一定的差异。
综合以上几点,笔者认为逸诗《多薪》应该属于楚地之作,且未经“采风”的修饰。
二、《采风曲目》
《采风曲目》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唯一一篇歌诗的作品,其中明确记载了先秦时期的歌诗曲目和曲调,对研究当时的采风之制及其详情、《诗》文本的结集情况有着重要的价值。《采风曲目》释文如下:
又 ,《子奴思我》。宫穆:《硕人》,又文又
,《子奴思我》。宫穆:《硕人》,又文又 。宫巷:《丧之末》。宫讦:《疋月》,《野又葛》,《出门以东》。宫
。宫巷:《丧之末》。宫讦:《疋月》,《野又葛》,《出门以东》。宫 :《君寿》【简一】
:《君寿》【简一】
□》,《将美人》,《毋过吾门》,《不寅之媑》。徙商:《要丘》,又 ,《奚言
,《奚言
不从》,《豊又酒》。 商:《高木》。讦商:《
商:《高木》。讦商:《 【简二】
【简二】
□》。讦徵:《牧人》,《场人》,《蚕亡》,《□氏》,《城上生之苇》,《道之远
尔》,《良人亡不宜也》,《弁也遗玦》。徵和:《辗转之宾》【简三】
□》,《亓翱也》。 羽《之白也》。
羽《之白也》。 羽:《子之贱奴》。讦羽:《北野人》,《鸟虎》,《咎比》,《王音深谷》。羽
羽:《子之贱奴》。讦羽:《北野人》,《鸟虎》,《咎比》,《王音深谷》。羽 :《嘉宾慆憙》【简四】
:《嘉宾慆憙》【简四】
居》,《思之》,《兹信然》,《技诈豺虎》【简五】
《句吴君毋死》【简六】
《采风曲目》共六简,残损较为严重,其中涉及到众多的先秦曲目,据马承源考证为39篇。这些曲目均类似于《诗经》中的篇名,但除第一简中乐曲篇名《硕人》与今本《诗经》中的《卫风·硕人》篇名相同外,其余均未见于《诗经》。从曲目的篇名上看,《采风曲目》中的一些曲目相当通俗,例如《子奴思我》《良人亡不宜也》《野又葛》等等,多为表达相思爱慕以及幽怨等情感的曲目,从篇名可以推测其内容的流俗趣味。
《采风曲目》展现了先秦时期用于诗乐舞演奏的最初的文本形态,前四简中记载了先秦时期的音阶名。在乐曲篇名之前加宫、商、徵、羽四个声名,而在声
名之后又均加类似于变化音或者偏音的前缀或后缀单字。声名包括宫、商、徵、
羽;音调名包括穆、巷、讦、和、徙、 、
、 、
、 、
、 等九个音区或者音位名。
等九个音区或者音位名。
此外,从第一简到第四简中的每一简,分别以声名宫、商、徵、羽为核心。《采风曲目》中这种情况的存在绝非偶然。楚简中的声名,不是位于诗歌篇名之后,而是位于诗歌篇名之前。因此,声名处于乐曲篇名之前,它就有着一定的特殊意义,可能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标识,以表示相关乐曲的调名,或者标识其中的一些变化音。
由此可见,《采风曲目》中不仅包含乐曲的曲名、调名以及变化音,还包括乐曲的乐谱和节奏,这些乐曲曲目均是可以入乐的。据《乐记》记载:“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由此可见,当时的诗的确是可歌唱可演奏的,而所奏乐器应该以弦乐器为主。
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采风曲目》中曲目的调名,应该是类似于诗歌歌唱和演奏的调式。同时,简文注重于乐曲曲调调名、调式以及节奏等的记载,而乐曲曲目本身并非记录的重点,曲目篇名仅仅是列举的符合此种调式的例子。此外,这些调名是对当时所采集到的诗歌格式和诗歌填词制谱的曲调的一种归纳性的总结,应该是记载采风的曲目目录。从整体上看,这篇诗乐记录非常的有条理,其形制也已经较为完善,它可能是楚国“采诗官”记载采诗乐曲的档案资料或者残本。
此外,传世文献中记载了西周至春秋时代和汉代采诗的情况,而未见战国时代的歌诗记载,竹书《采风曲目》的出土,填补了战国时代采诗的空白,其研究价值重大。
第三节 清华简中逸诗
清华简《旨阝(耆)夜》简文披露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旨阝(耆)夜》简文共14枚竹简,在其最后一支竹简简背写有篇题“旨阝(耆)夜”。简文中的《乐诗》,现已知公布四首,除《蟋蟀》外,其余三首均未见于传世文献,其价值是不可忽视的。有学者推测,《乐经》在秦“焚书坑儒”之后亡佚,而《乐诗》恰恰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劝酒乐诗,极有可能是《乐经》中的篇目。故此,李学勤认为这部分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无疑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发现。”目前这部分竹简虽有个别残缺的地方还未考定出来,但基本上已经完整。
简文主要记述了武王八年征伐耆(黎)国,得胜归来,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参与典礼者主要有武王姬发、毕公姬高、周公姬旦、召公姬奭、辛公甲、作册逸、吕尚父姜望等。在典礼上,按照礼的规范与要求,饮酒赋诗,简文的内容就是记载“饮至典礼”上的诗作。
由于现已公布的竹简资料有限,文章以下仅对这四首古逸诗进行解读。
一、《耆夜》中的乐诗
诗乐舞一体,在典礼上赋诗、作乐作为一种古礼,在战国时代较为常见,根据现已公布的关于清华简的有限资料,已知在“饮至”典礼上所赋的诗有《乐乐旨酒》《英英戎服》《明明上帝》《蟋蟀》。
《乐乐旨酒》:
乐乐旨酒,宴以二公;
任仁兄弟,庶民和同。
方壮方武,穆穆克邦;
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诗篇主旨非常明确,即“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二公”应该指毕公与召公,表达了武王对戡黎战争胜利的喜悦和对毕公、召公的赞扬和期许,同时寄托了武王“嘉爵速饮,后爵乃从”的愿望。
《英英戎服》:
英英戎服,壮武赳赳;
毖精谋猷,裕德乃究。
王有旨酒,我弗忧以浮;
既醉又侑,明日勿修。
这首诗歌表达了周公对毕公以及全体将士的高度颂扬和赞许,称赞他们善于征伐,威武雄壮。整首诗既展现了周公的高度热情,“王有旨酒,我弗忧一浮”;又表现了其理性的一面,“既醉又侑,明日勿修。”
简文中武王与周公分别作诗致毕公姬高,以表达征伐黎国胜利的喜悦之情,颂扬毕公高的威武。根据《周本纪》记载,毕公,名高,周文王的第十五子,武王之弟。武王灭商之后,将其封在毕地,故称毕公。“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为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成王临终时,托付召公和毕公辅佐康王即位。在毕公高等人的努力辅佐下,西周进入了鼎盛时期。在古文《尚书·毕命》中,康王高度赞赏了毕公的功绩。由此可见,毕公在西周前期地位之高与功绩之卓著。
《明明上帝》:
明明上帝,临下之光;
丕显来格,歆是禋盟。
於……月有盛缺,岁有歇行;
作兹祝诵,万寿亡疆。
据简文记载,这首诗歌是周公旦祝颂武王的诗,他祝愿武王及其周王朝“万寿亡疆”。诗作中充满着对武王极高的赞誉和无限美好的祝愿。
此外,根据清华简的记载,在“饮至”典礼上,“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周公听到蟋蟀的叫声,于是作《蟋蟀》诗一首。简本《蟋蟀》分三章,然而第一章、第三章尚有残缺,只有第二章简文基本完整:
蟋蟀在席,岁聿云茖。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廴。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愳。
此诗意在表达劝诫,告诫诸侯不可耽于欢乐而忘记前途的艰难。
二、《耆夜》中乐诗献疑
简文记载的乐诗,出现了诗篇的具体作者,即武王与周公,而诗篇具体作者的出现、商周时期国君赋诗的事例,在传世文献中并不可考。李学勤《清华简〈旨阝夜〉》、沈建华《“武王八年伐耆”刍议》、孙飞燕《〈蟋蟀〉释读》、马楠《清华简〈旨阝夜〉礼制小札》以及曹建国《论清华简中的〈蟋蟀〉》等文章,都基本认同简文所记载的历史史实,并且赞同简文《蟋蟀》为周公所作。
但是,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有待商榷。
(一)《耆夜》乐诗与《穆天子传》中诗篇比较
西晋初年魏墓出土的先秦简牍《穆天子传》,卷三所载与西王母唱和之诗、卷五载周穆王所作三章哀民诗,在《诗经》中未见,但与西周时期诗作风格无异。为方便下文论述,附录《穆天子传》中的诗篇如下:
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成群。于鹊与处,嘉命不遵,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称顾世民之恩,流涕芔陨,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
我徂黄竹,□员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旦夕勿忘。
我徂黄竹,□员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旦夕勿穷。
有皎者(乌各),翩翩其飞,嗟我公侯,□勿则迁。居乐甚寡,不如迁土,礼乐其民。
清华简中四首乐诗与《穆天子传》中诗篇的风格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有着多处共同特征。首先,具体作者的出现,且出现国君赋诗。清华简乐诗出现具体的作者,即武王与周公;《穆天子传》诗篇也出现了具体的创作者:西王母与周穆王。其次,每首诗篇前都带有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小序。第三,诗篇押韵工整。清华简四首乐诗为整齐的四言诗,且用韵工整:《乐乐旨酒》韵读:东部—公、同、邦、从;《英英戎服》韵读:幽部—赳、究、浮、修;《明明上帝》韵读:阳部—光、盟、行、疆。这三首古诗的韵律都为隔句押韵的句尾韵,且它们用韵都非常的精准工整。简本《蟋蟀》第二章韵读:鱼部—席、茖、夕、愳,属于首句入韵而后隔句押韵的句尾韵。《穆天子传》四首诗作中第二首与第三首押韵工整。第二首诗韵读:鱼部—土、夏、汝、野,真部—均、年,属于首句入韵而后隔句押韵的句尾韵。第三首诗韵读:鱼部—土、野、处,文部—群、遵、陨,阳部—簧、翔、望,基本符合首句入韵而后隔句押韵的句尾韵。第四,清华简四首乐诗,除《蟋蟀》外,其他三首诗篇与《穆天子传》中的诗篇,均未见于今本《诗经》,但其风格与西周诗作无异。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清华简中乐诗与《穆天子传》中的诗篇,风格特征极为相似,这些古诗都是伴着具体历史事实而出现,并带有说明性的文字,类似于《诗小序》。同时,诗篇不仅出现了诗作的具体作者,而且赋诗作者中出现了周天子。此外,诗作风格与西周时期的诗作无异,诗篇押韵也较为工整。
根据学界的研究,《穆天子传》应该是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的时代,与周穆王同时或者稍后的史官,以史为题材缀合的周穆王西游昆仑而见西王母的历史故事。通过上述清华简乐诗与《穆天子传》诗篇比勘,笔者认为清华简《耆夜》简文的性质应该与《穆天子传》的性质类似,其最大的可能应该是战国中晚期,楚士缀合多首古诗与历史故事而创作的。
1.简文中类似小序的文字与《诗小序》比较
关于《诗小序》,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认为,它明显的分为两截,古人一般将这两截分别称为“古序”“续序”。所谓“古序”,就是每首诗开头用于说明诗旨的文字;所谓“续序”,也就是“古序”之后的具体说明,类似于对“古序”的注解文字。两者所产生的时代并不相同,但意思却相辅相成。例如《唐风·蟋蟀》的小序云:“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诗以闵之,欲知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用无礼,乃有尧之遗风焉。”很明显,在《唐风·蟋蟀》的小序中,第一句话和后面的语句分成两截,第一句话是概括诗旨,后面的部分主要是对第一句话的注释。而小序将诗旨概括为“刺晋僖公”,带有很明显的穿凿附会的色彩。我们纵观《诗小序》,其文字内容多为附会历史史实,注解牵强,故此学者多认为《诗小序》不足为信。朱熹云:“《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郑振铎云:“《毛诗序》最大的坏处,就在于他的附会诗意,穿凿不通。《毛诗》凡三百十一篇,篇各有序……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附会的,是与诗意相违背的。”
《诗小序》是战国至汉初形成的关于《诗》的附会史事的注解,而同为战国时代的《耆夜》乐诗中也出现了类似于《诗小序》的文字。我们将《诗小序》作为参照,通过两者的比勘,完全可以认为,《耆夜》采用的手法与《诗小序》的笔法一致,将一些诗与历史上的某人某事比附起来,说这些诗篇是为某人某事而创作,把诗歌当做史书的注解,或者比附史事。故此,笔者认为《耆夜》是战国楚士比附史事,将多首古诗进行历史情节编缀而创作的,其历史可信度较低。
2.简文《蟋蟀》与今本《唐风·蟋蟀》比较
为方便对读,附录简本《蟋蟀》与今本《唐风·蟋蟀》如下:
蟋蟀在席,岁聿云茖。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廴。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愳。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以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简本《蟋蟀》与今本《唐风·蟋蟀》两者相类似,但在语词、用韵以及四言体上今本《蟋蟀》更为完善。例如在用韵上,简本《蟋蟀》第二章韵读:鱼部—席、茖、夕、愳,首句入韵而后隔句押韵的句尾韵。今本《蟋蟀》三章韵读分别为:鱼部—莫、除、居、瞿;祭部—逝、迈、外、蹶;幽部—休、慆、忧、休,隔句押韵的句尾韵,押韵工整。在四言体上,也非常的明显,今本《蟋蟀》更为严格完整。简文《蟋蟀》应该是今本《唐风·蟋蟀》的祖本,经过“采风”之后,对祖本《蟋蟀》进行加工整理,甚至是多次的修订,最后使其在语词、用韵以及四言体上更为整饬。但简本《蟋蟀》在“采风”之后依旧流传,并被学者士大夫记载于典册之中,所以有幸保存下来。而清华简《耆夜》作为战国楚士整合诗歌所编缀的历史史事,简文中出现的《蟋蟀》作者周公,可信度较低,正如后现代史学理论认为,历史本来就是“一种冒充成真实生活情况的构思”,是“一种杜撰或虚构物,一种对过去的描述而非反映”。因此,以附会史实为背景的文献(清华简《耆夜》),我们只能将其作为研究的参考,不可以当做信史对待。
第四节 简牍中零散的逸诗
出土简牍中除了上述相对较为完整的逸诗诗章外,还存在一些零散的先秦逸诗,如下:
(一)仅存零句的
1.吾大夫恭且俭,靡人不敛。
2.大明不出,万物皆暗。圣者不在上,天下必坏。
(二)仅存篇名的
1.《律而》
2.《河水》
由于竹简残缺严重,对上述零散诗句或篇名的诗评不够完整,很难断定它们为逸诗还是与今本毛诗异名而同篇的,此处姑且暂定为逸诗。文章只是将它们单独列出,不妄加论述。
编辑:赵露晴 初审:刘雯 复审:俞林波 终审:张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