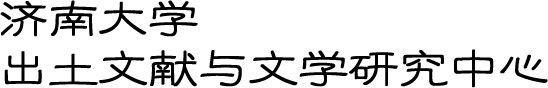写在前面的话
刚接触古典文献学,我们有可能会对其心生敬畏,觉得这门学问有些“高冷”,其实这门学科既不是那么热门,也不是那么冷门,而且一旦登堂入室之后,还会感觉到这门学问是很有“温度”的,是那么可亲可近,然后恍然发现,原来古典文献学这门学问就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学习的很多学科或专业是建立在该门学问基础上的,只是日用不知而已。古典文献学这门学问确实有可能令我们产生一些“错觉”,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受其一些表象所遮蔽。这种遮蔽可能是惯常的,也并不那么奇怪,比如,我们对于中国乾隆皇帝(1711-1799)与美国总统华盛顿(1732 ---1799)所处时代的感觉可能会不一样,其实他们中并不是一位是古人,一位是现代人,而是同一时期的人,且于同一年去世。所以,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古典文献学这门学问,她既不“高冷”,也不“热门”。我们现在的责任和任务就是要认真学好这门学问,充分运用与发展这门学科,而不是数典忘祖,浅尝辄止。
一、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
顾名思义,古典文献学是以古典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这一研究对象不免就显得有些“古老”了;而真正的古代读书人并不会对于这门学问有“隔世”之感,而只会视之为读书人必备的应知应会的知识。然而,今人要真正掌握这门学问,却也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
古人很早就开始传播与保护文献。倘若说文献既包括文字类型也包括口头类型的话,那么古人文献意识的产生是很早的,可以说是与语言和文字的诞生相同步的。远古神话最早都是口头文献,如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女娲补天,由于人们口耳相传方才流传至今。我们现在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录的文献应该是甲骨文献,古人为了收藏这些文献也肯定想了不少办法,如号称“中国最早档案库”的殷墟YH127就窖藏了17000余片甲骨,而今都成了无价之宝。古代官府很早就设置了有关文献之官,有求书之官,有校雠之官,有编纂之官,有守藏之官,如老子做过周守藏室之史官,当然也就不乏收藏文献的所谓“金匮石室”,如汉室宫廷藏书的天禄阁与石渠阁。
古人不仅珍视文献收藏,而且还重视文献整理与运用。《诗》《书》《礼》《易》《春秋》这些古代典籍无不历经古人的多次整理与编纂,无论是其早期写本还是其后期版本大抵无不如此。春秋时期的孔子不但深知文献之重要价值,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还是文献整理的躬身实践者,《孔子家语·本姓解》记载“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中国历史上,即使有焚书之厄与经籍之变故,但都不能阻滞古人对于文献的保护与传承。
古人深谙古典文献学问之道。从学术史角度来看,作为一门学问,中国古典文献学的起源是相当早的。孔子整理“六经”就已经表明了他在古典文献学方面的造诣,所以后世尊奉他为中国古典文献学领域的一位显赫的远祖。汉代刘向奉命领校国家藏书,“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编制《别录》《七略》(刘歆完成)等目录学经典之作,又可谓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开路先导。
古人擅于总结和升华文献学理论。南宋时期郑樵是最早以专著《通志》形式讨论古典文献整理工作的学人,如言“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通志·总序》)。他在《通志·校雠略》中阐述了文献收集、分类编目、流通利用等文献学问题,如其言“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郑樵以后,系统研究文献学理论的当为清代的章学诚,著有《校雠通义》,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著名文献学观点,并言“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当然,古代读书人大都熟知古典文献学问之道,否则难入治学之门径,犹如盲人不识其途,更罔谈入其堂奥。这正如清人王鸣盛所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十七史商榷·卷一》)“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十七史商榷·序》)文献可谓是人类文明的全纪录。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薪火相传,古典文献是功不可没的,古人对于古典文献的重视更是功莫大焉,因为古人早就懂得“欲要亡其国,必先去其史;欲要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的道理。
二、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年青的学科
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其实滥觞于17世纪的西方科学革命。自从清末采取西式学堂之后,国人才逐渐引入西方的“学科”这一知识分类体系以及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组织形式的概念。近现代以来,我们按照西方的学科范式建立了大量的新学科,当然这些学科名称大都来自于移译,如文学、哲学,只有像中国古典文献学这样的个别来自于国人新创,但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相对于近现代其他学科来说诞生得较晚。
1920年首现“文献学”一词。1920年10月梁启超费十五日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次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此书原是为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一书所作之序,脱稿后却独立印行,并取得了很多“意外收获”,既成就了有关清代学术的第一部专著,又首创了“文献学”一词。但此时的“文献学”还没有成为一门专门学科的专有名词。
1928年首现第一本文献学著作。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撰写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被称为“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 “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通志·总序》)郑氏兄弟第一次构建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体系,虽不乏草创痕迹,但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至此,文献学开始转向一个带有学科性质的专有名词了。
1957年大学首开文献学课程。1957年王欣夫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开设“文献学”课程,虽然设定为选修课,但这也是“文献学”作为一门课程在高校开设的首例。当时,“文献学”应该是一门前沿性的学问,也是一门开创性的课程。后来,王欣夫于1957年至1960年间在讲授“文献学”课程时的讲稿以《文献学讲义》之名出版。
1959年大学首设古典文献学专业。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负责推进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并催生了中国第一个古典文献专业。1959年北京大学首创中国古典文献专业,并招收了第一届学生,这意味着古典文献学正式成为了一个学科,古典文献专业成了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教学基地。
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为一个交叉、兼综的学科,“文革”之后不断地得到发展壮大,而今枝叶繁茂,欣欣向荣,焕发着一门既是古老学问又是年青学科的风采。
三、中国古典文献学的鲜活叙事与想象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内容既不是大量的资料堆砌,也不纯粹是枯燥的理论推演,而是不乏鲜活叙事与学术想象力的学科。当学习与研究古典文献学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叙事中直面学术问题,可以在历史维度中建立结构联系,可以在理解中展开丰富的想象,这样方可把个人置身于学习与研究之中,获得个人难得的学习与研究体验,一改世人对于古典文献学的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
文献载体上萦绕着人的精神。文献载体不仅仅是客观的物质,而是有人类的精神萦绕其上的“生命体”。这些载体承载着不同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功能,被世人艳称为陶泥时代、甲骨时代、青铜器时代、简帛时代、纸张时代、电子时代。遥想不同的载体时代,我们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想象。陶泥载体的每个彩陶,每块刑徒砖,每枚封泥,都可能诉说着一个传奇的故事。甲骨时代每片甲骨都可能刻写着一个宏大叙事,也许是一场战争,也许是一次灾荒,也许是一个祭祀典仪。至于被誉为“甲骨文之父”的京城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发现甲骨文以及后来的甲骨考古发现背后的故事更是令人唏嘘。青铜时代的每件铜器都可代表着我们的青铜文明,祈望着“子子孙孙永宝用”。简帛时代流传着“韦编三绝”的故事,至于1942年发现的“楚缯书”辗转流落到异域的跌宕波折,更是令人着迷。纸张时代的造纸术由东向西传播,使西方文明为之焕然一新。至于公元751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部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将军沙利会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后,造纸术成就了中亚重镇撒马尔罕成为阿拉伯帝国第一个造纸中心,然后再传到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埃及的开罗和摩洛哥,这一造纸术传播路线不知播撒了多少动人的故事。而今电子网络时代到处是人类创造的奇迹,时时是不断更新的世界。我们研究这些载体的流变,不仅仅是回溯这些器物演变历程,而更重要的是重温人类的精神发展史。
文献造伪与辨伪相生相灭。书籍有真伪之分,作伪者或为托古,或为炫名,或为邀赏,或为渔利,亦着实不易;后人再作辨伪,真是探赜索隐,犹如侦探一般。造伪者故事离奇,辨伪者伤透脑筋。汉时人张霸空造《尚书》102篇,比足本百篇还多出2篇,称之为春秋之前旧物,献之成帝。成帝大喜,赐给张霸博士官(梁启超说,这相当于现在国立大学教授)。后来帝出秘籍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有人认为张霸罪当至死,成帝深爱其才,又怜他造假不易,仅革博士职,饶他一命。张霸造伪流毒很广,“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论衡 正说》)后来,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献伪《古文尚书》,该书前还添加一篇伪造《孔氏传》。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及《孔氏传》不但立为官学,而且成为今文(伏氏)传本、古文(孔氏)传本之外的第三种传本。后世学者辨伪,穷追不舍,成累代奇观。南宋吴棫著《书稗传》,始疑梅氏献本《尚书》不是古本,朱熹亦表示疑惑。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推测梅传《尚书》应是魏晋间人所作。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列出128条论据(今存99条)证梅传《尚书》之伪。今清华简问世最终定讞梅传伪《尚书》之学术公案。每一次文献辨伪都是“破案”方与“作案”方的博弈,至今还有许多这类古文献“迷案”有待来者。《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诚宜哉!
文献典藏与散轶有着背后博弈。文献典藏与散轶往往都是社会各种力量在起到重要作用。历代藏书的场所,都藏着许多掌故轶事。天禄阁,是汉丞相萧何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195年)监修未央宫的同时修建起来的,与石渠阁东西相望,二者都是藏图籍处贤才所在地。古代书院大都兼做藏书之所,最早书院起初还是官办的“修书之地”,每所书院又都是大德之人会聚讲学之处,如“鹅湖之会”传颂至今。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中每座楼都值得书写出一篇感人的“传记”,都有讲不完的故事。有藏书,就会有书厄,秦始皇下焚书之令为首厄,然后有王莽之燔宫、董卓之祸乱、刘渊、石勒(274年―333年8月17日)之陷洛、萧绎之毁书,这些都是政治力量所为。历朝历代的文献典藏与散轶都是与国家政治走向和社会状况紧密相连的。
训诂可以在旁证叙事中活泼起来。训诂不尽是特别枯燥无味的事情。我们古人对于中国方块文字的研究派生出三大学问,简略说来,相对其发音,衍生出音韵学;相对其形,衍生出古文字学;相对其义,衍生出训诂学。当然,传统训诂学解释词义的方法也有三种,分别是形训、声训和义训。形训有点儿像图像学解释。《尚书》中有“王若曰”,这“若”字作何解?后世诸儒解释往往不得其真谛。其实,“若”字原字形就像一位在通天地情形下的大巫师形象。在巫教盛行的时代,王本身就是大巫师,其言就是神明之言,犹如后世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由此看来,“若”就表明通神明之义。《尚书》还有所谓语气词“隹”,即“惟”,如“惟天生民有欲”“惟天生聪明时乂”(《商书·仲虺之诰》),“惟皇上帝”(《商书·汤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商书·伊训》)。其实该词并不是语气词那么简单,“隹”代表商人的玄鸟图腾崇拜情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帝”等字皆衍生于玄鸟之形。
学习与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离不开想象力,古典文献学也不例外。我们应该挖掘古典文献学中的鲜活事例与微妙叙事,增加我们学习与研究的兴趣,丰富我们的学习与研究的想象力,开拓出一片令人歆羡的局面。
四、中国古典文献学与现代化挑战
中国古典文献学根植于传统的土壤,但不仅仅是属于过去,而且还属于当下和未来,当我们社会发展的步伐走得愈远,我们就应该愈加反顾过去,中国古典文献学在这种反顾中也就愈加需要充当好自身应该担负的角色。然而,中国古典文献学也会遭遇到现代化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但只要与时俱进,前景必定会一片光明。
传统目录学在近代首先遇到了西方学科学的冲击。在传统目录学中,当四部分类法占据主导地位之后,经史子集,总括群书,这反映出我们传统的知识分类体系。近代以来,西方“学科制”概念引入中土后,直接冲击中国原有的传统目录学,虽全然看不到刀光剑影,却杀机四伏,结果导致1901年和1905年废除建立在传统目录学基础之上的书院制和科举制,代之以建立在学科基础之上的学堂制和学分制,“从教育史角度来看,如果说1905年废除科举制预示着清政府覆灭的话,那么这也可以说清政府的覆灭是‘学科制’催生的结果”。传统只可延续,不可摧毁,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运用西方学科制去肢解传统知识体系,也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目录学体系去硬框西方现代知识体系,而应该各自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和适应的领域。
传统古籍典藏与电子文库的文献储藏方式可以相互借鉴,并行不悖。传统古籍的收藏方式确实会遇到很多难题,如占用大量的配置有装备条件的空间,既要防潮、防霉、防虫、防火,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予以保护,而现代电子文库则可以大大地带来保护与使用的方便,所以我们应该允许传统古籍进行数字化保存。但是电子文库也不全是神丹妙药,也存在不足,如果没有阅读工具,那就没有办法阅读文库;当保存软件更新升级之后,如果没有这款软件,那就再也不可能打开这个文件;如果遇到黑客攻击,那也有可能损失惨重。传统文献有版本的问题,电子文献也有质量问题。既然纸质文献与电子文献各有利弊,那么也就不可偏废。
传统文献索引当下遇到了电子文献检索。文献检索是文献使用的重要的工具、方法与途径。传统文献索引的编制只能依靠人工,耗时费力,且不便于使用,如叶圣陶当年编制《十三经索引》花了很大工夫也只能编成逐句索引。我们现在不能抱残守缺,而应该使用电子文献检索工具,瞬间就可以检索到我们需要的文献信息。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文献检索发展的历程,今天发展的成就都是建立在昨天基础之上的。
任何学科都是在不断的挑战与响应中获得愈加完善,都是在与时俱进中获得愈加发展。我们学习与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就应该敢于接受各种挑战,在挑战中获得各种机遇。
五、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古典学之重建
中国古典学的重建既引起了当下学界的广泛兴趣,也成为了当下学界的一种呼声。不可否认,古典学的原初说法来自于泰西,而且古典学一直是西方最主要的人文学科,时至今日仍然是西方人文学科的基石。但是,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在中国与西方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西方,其源头可追溯至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学者们对古代希腊文献的校勘和整理。在东方,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孔子对于六经的整理与教育。西方古典学主要是对于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开展研究,为西方文明找到其发展的源头和不竭的动力源。中国古典学也就应该针对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秦汉文明开展研究,为东方文明找到发展的源头和强劲的动力源。我们要重建中国古典学,就必须建设好中国古典文献学,因为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中国古典学重建的基础。
中国古典学应该是对于上古时期的典籍及其上古时期物质和精神层面文明进步的研究,其中典籍是其重要的研究对象,甚或说是其核心组成部分,裘锡圭甚至认为“似乎也未尝不可以把‘古典学’的‘古典’就按字面理解为‘上古的典籍’”。我们既有传世的上古时期典籍,又有上个世纪以来大量出土的上古时期文献,为我们的古典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资使用的资料。中国古典学重建大有可为,也具有巨大的学术发展空间,但这也为我们中国古典文献学学习者和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要成为中国古典学重建的积极参与者、重要贡献者。中国古典文献学者和中国古典学者既承担着中华文明守望的责任,也肩负着中华文明延续、弘扬和创新的使命,虽然这两个领域的学者有些与古为徒的味道,但重要的是也要体现出现代性,因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典学也是属于现代性的事业。
历史不同于过去,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传统都是当下的,我们要让传统犹如河流离开其源头愈远就越加汹涌澎湃;古典是相对于后世而言的,我们要将古典成为心中的崇尚的对象和未来发展的不竭动力。观看世界发展大势,浩浩汤汤;审视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生机盎然;我们中国古典文献学事业发展恰逢盛世,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与伟大复兴将为中国古典文献学者带来光明前景,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这黄金时代的一切伟大事业添砖加瓦吧!
蔡先金
2020年1月5日星期日于济南无影山寓所
绪论
文献起源之早,可谓与人类知识萌生同步,而后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之中,乃构成了人类全部知识学重要基础条件之一。中国是世界文明四大古国之一,拥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华夏文化是东方文明的典型代表,当西方人言必称希腊的时候,东方人理所当然地可以言必称华夏,乃至现代诺贝尔奖获得者们亦认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遥远的华夏,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无论是希腊文明还是华夏文明,作为世界文明史中的双子星座,两者都毫无疑问地坐拥最为丰富的古典文献。这些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既然要正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掘它们蕴涵的现代性力量,并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那么就不能忽视对于古典文献的学习与研究。
第一节 文献与文献学释义
概念是语言的单元,承载者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思考,“我们掌握和发展概念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获得人和事物的意义,并与他人进行交流。显然,其中有些概念比另外一些概念更加重要。那些关键概念使得我们能够探索各种各样的情境和事件,寻找到有意义的联系。”关键概念的演变是人类思想变革的表征,而人类思想变革却永远不会停止,所以每个关键概念皆会包含着历史性的转变潜力。文献与文献学当然就应该属于所谓关键概念,并蕴含着历史性的力量。
一、何谓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论语·八佾》载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东汉郑玄注:“献,犹贤也。”而许慎《说文解字·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宋代朱熹《论语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这是古人对于“文献”这一合成词的最早解释。在古代,特别是上古时期,知识文化的传播除了依靠典籍之外,还要依赖于口耳相传这一重要途径。元代马端临始用“文献”名其书,即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文献通考》。马氏在《文献通考·自叙》中指出:”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叙事本于文,因文为客观记录;而论事采于献,因献为主观思想。由此看来,马端临还是在沿用文献的传统之义。
语词的语义是会发生流变的。明清时期,“文献”一词常用于专指典籍,如明初编的《永乐大典》,原名为《文献大成》。这种对于“文献”语词的理解一直影响到后来。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撰写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被称为“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同样是建立在文献作为古籍理解的基础之上。当然,过去文献学家对于“文献”的理解与定义还是略有差异的,比如刘师培在《文献解》中说:“仪献古通。书之所载谓之文,即古人所谓典章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王欣夫在《文献学讲义》中认为:“文之与献是不可分割的。因而后来凡是历史性的材料都称之曰‘文献’。”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中指出:“过去封建学者们所强调的‘征文考献’,便是说要了解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取证于书本记载,一方面探索于耆旧言论。”总之,通过对于“文献”作词源及其流变考稽之后,传统古典文献学家对于“文献”概念的理解最终还是指向典籍的记载与宿贤的言论,差别仅存在于广义与狭义之间。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献”的定义也显露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1983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从国家标准的制度层面给“文献”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其基本要素包括:(1)记录是构成文献的手段;(2)知识是文献的内容;(3)载体是文献的形态。而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情报术语国际标准》(ISO/DIS5217)对“文献”的定义是:“在存贮、检索、利用或传递记录信息的过程中,可作为一个单元处理的,在载体内、载体上或依附载体而存贮有信息或数据的载体。”实质上,国际化标准组织对于文献的定义与我们国家标准定义之间并不矛盾。无论如何,文献之定义是不能缺少两个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一是要有一定的知识或信息内容,没有记录任何知识或信息内容的纸张、磁带等载体不能成为文献;二是要有用以记录知识或信息的物质载体,没有载体的知识亦不能称之为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知识或信息不能称之为文献。因此,现代文献学家可以给出“文献”这样的定义:文献是指那些将知识、信息用文字、图像、数码等各种符号,通过书写、印刷或其他诸如光学、电磁学等方法记录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结合体。随着信息时代之来临,文献认识、文献处理和文献传播方式在新的科学技术推动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正在开辟文献学的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何谓文献学
“文献学”一词首现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后来他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初史学之建设”》中以己之见解释了一下“文献学”:“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梁氏具有文献学点题之功,却无发凡起例之实。
中国古代虽无“文献学”之名,但历代学者却积累了大量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的经验,应该说,自从有文献开始就有了文献整理相关工作了。从学术史角度来看,作为一门学问,中国文献学的起源却相当早,至春秋时期,孔子整理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主的古代典籍,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学问,因此从某种角度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著名文献学家。从那以后,2500多年来,历代学者整理文献的成果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所积累的文献学知识也就越来越丰富;如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制《别录》、《七略》;郑玄为群经作注。最早以专著形式讨论有关文献整理工作的是南宋的郑樵,他在《通志·校雠略》中阐述了文献工作中的文献收集、分类编目、流通利用等问题。郑樵以后,系统研究文献学理论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著名观点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要求在文献整理过程中要明确反映并细致剖析各种学术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及相互关系等。但他和郑樵一样,都把这些工作称为“校雠学”。为了收集、整理、交流和利用文献,学者们就必须对文献的特点、生产方式和整理方法等予以探究,从中总结出规律,从而自觉与不自觉地为文献学的形成作贡献。所以说,文献学是在文献工作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自成理论体系的中国文献学或者说具有现代学科体系性质的中国文献学却产生得很晚,于20世纪初才出现。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始以“文献学”名书。郑氏定义“文献学”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此后因内忧外患,连年战乱,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未能引起重视。1957年至1960年王欣夫写就《文献学讲义》,并在复旦大学开设“文献学”课程,这是新中国高校在“文革”前开设“文献学”少有的例子。王氏认为“文献学”“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其内容应该是目录、版本、校雠三位一体。1980年代初,张舜徽撰写《中国文献学》并在华中师范大学开设该课程;吴枫撰写《中国古典文献学》,并在东北师范大学开设该课程。此后,以“文献学”或“文献”字样名书的各类著作和教材层出不穷。文献学界也积累了发展文献学学科的丰富经验,为新时期学科体系的改革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文献学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和分布、发展规律、文献整理方法及文献与文献学发展历史等。文献学可分为许多分支学科,如从文献形式角度,可分为目录学、校勘学、典藏学、辨伪学等;从文献载体角度,可分为石刻文献学、简帛文献学、电子文献学等;从学科文献角度,可分为历史文献学、经济文献学、化学文献学、法律文献学等;从类型或特定文献群角度,可分为佛教文献学、戏剧戏曲文献学、敦煌文献学、出土文献学等;从时代角度,可分为古典文献学、现代文献学等。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分工以及学科分类会越来越精细,文献学学科分支也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各种各类新学科文献会涌现出来。
三、何谓古典文献学
古典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一般所说的中国古文献,实际是指汉语古文献,所以古典文献学全称应为中国古典汉语文献学。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群书,把同一种书的不同的本子进行校雠,缮写出比较完备的本子,同时撰写叙录,也就是撰写提要,然后编纂出所有书籍的分类目录,以揭示学术源流,并供查考之用。刘氏父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古典文献学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后人用广义的“校雠学”来阐释刘氏父子所开创的学问,也就是将目录、版本、校雠三者统统塞进“校雠学”的大口袋中。于是,校雠学就几乎成了古典文献学的别名。宋代郑樵《通志·校雠略》、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当代程千帆与徐有富《校雠广义》均沿用校雠之名。为了区别于现代文献学,故有古典文献学之名。古典文献学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古典文献学实际就是传统校雠学的延伸,即目录、版本、校勘。广义的古典文献学则包括辨伪、辑佚、考证、小学等多方面。
古典文献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进行各种分类,比如从学术角度来分,古典文献学可分考据之学和义理之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之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之学;从研究内容方面来看,古典文献学可分为古文献的形体(包括古文献的载体、体裁和体例)、古文献整理的方法、古文献学的历史、古文献的理论等四个方面;从历史纵向角度,古典文献学史又可分为先秦起源期、汉代奠基期、魏晋至隋变迁期、唐五代发展期、宋代兴盛期、元明中衰期、清代复兴期、近代以来总结期。
古典文献学是个交叉、兼综的学科,以传授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研究与整理的知识为任务,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二级学科的古典文献学,在学科分类中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包括了文学类、语言类和文献类三类基础课程,可称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三驾马车。冯浩菲先生认为古典文献学具有综合性、边缘性、交叉性、服务性四个明显的特征,现可总结为:(一)综合性。这门学科内容相当丰富,包含了与许多现行的不同层次的独立学科有关的各种知识。(二)基础性。这门学科与其它各门学科都有关系,各门学科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献的演变造成了文献学发展的资料基础。(三)交叉性。这门学科所属的各种应用文献学著作在体例上有不同程度的交叉现象。(四)服务性。这门学科从整体上来说除了保留其独立性之外还是为其它学科的发展服务的。古典文献学可谓是一门冷学,并不像有些学科那样炙手可热。然而,文献学却又是一门显学,因为没有任何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能够离开文献学。
《拉封丹寓言》中有首“农夫和他的孩子们”寓言诗,其中农夫说:“千万不要把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卖掉,因为财富蕴藏其中。”古典文献就是这样一笔遗产,一处金矿,不可视而不见,不可不深挖掘金。叶瑛曾说:“吾国学术,源远流长,载藉之富,甲乎世界;初涉其藩,茫无涯涘,不有书焉为之津逮,鲜有不兴望洋向若之叹者。”古典文献学知识是从事其它学术研究的基础,并为治学者指引获取文献、利用文献、整理研究文献的方法途径,因为从事学术研究,必然要从文献入手,离开了文献,便没有了基石,没有了根据。
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虽然研究对象略有不同,但是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现代文献学也是建立在古典文献学的基础之上的,而当古籍采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数字化之后,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之间也就打通了。古典文献学家既不会抱残守缺,反而会接受现代文献技术,并张开双臂去拥抱古典文献学的新时代。
第二节 古典文献学的功用
如果仅限于目前考古资料,从文献载体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史可分为“甲骨时代”“简帛时代”“纸张时代”“电子信息时代”,或者分为“书写时代”“印刷时代”“录入时代”。古典文献研究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核心内容。中华文脉相承,古典文献及古典文献学可谓功莫大焉。古典文献学不仅对于古籍整理意义重大,而且还可以为阅读提供指导,为治学提供门径。
一、目录学之功用
只要是想有目的地阅读某一类图书,就得知道应该阅读什么样的图书。古典文献学之目录学能够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全面、可靠、最佳的图书资料信息。什么样的文献学著作是一部好的著作呢?冯浩菲先生曾举例说明,比如一本好的《论语》文献学著作,首先应该将历代所出现的(倘条件许可的话还应该将国外汉学界自古以来所出现的)各种《论语》文献作一次尽可能全面、系统、得体的研究介绍。其次,应该说明关于《论语》的这类文献,哪些是可靠的,而哪些是不可靠的,原因何在。最后,还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分门别类,说明哪些文献最佳。如此等等。
古典文献学中的目录学是治学的门径。清王鸣盛认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曾说:“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点雅记,各适其用。”又,张之洞《鲭轩语·语学篇》“论读书宜有门径”条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人,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术门径矣。”古典文献学分出了“目录学”之分支,重点研究古典文献的分类,其旨大抵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前人对此多有共识,如宋郑樵说:“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通志·总序》)又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 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十七史商榷》卷七《汉书叙例》条)章学诚认为目录可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卷一《互著》)。南宋郑樵《通志·校雠略》云:“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目录学的重要功用可以概括为这样四点:一是阅读之向导;二是治学门径之指导;三是古籍整理之借助;四是古籍文化传承脉络之标明。
二、版本学之功用
版本学涉及文献文本的考察和鉴别。古籍流传愈久,版本也就会愈多。同一书籍既然有多种版本,那么也会存在好次之分,善本当然较为可靠,而劣本就有可能贻误学界了。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说:“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版本学可以揭示书籍不同版本的特点以及价值,版本不同,其特点有异,其价值也是不同的。版本学也是古籍整理的基础,因为古籍整理的关键就是选择一个好的底本,然后参校其它版本,整理结果方可信。只有懂得版本学的知识,读书治学方可有可靠的资料依据。同时,版本学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的一条重要途径。
三、校勘学之功用
图书有优劣之分,校勘学主要作用就是为人们读书治学提供符合或接近原稿的书面材料。鲁迅曾尖锐指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其实我国古籍代有散亡,一旦复出,存者多寡各异,其间错杂窜乱,曷可胜纪?即使流传之古籍,同样也会辗转至讹。鲁迅所指出的这些问题正说明校勘学之重要。校勘是读书、治学的先决条件,是取得正确文本的重要手段,诚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说:“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我们若要研究古代学术,就需要以校勘学为指导,具有独立校正古书错误的能力。校勘学还有利于古籍整理与出版,认真校勘就能为文化事业做出贡献,否则会造成损害。
四、辨伪学之功用
梁启超曾指出:“无论做那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的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辨伪就是辨识文献的真伪,包括书籍名称、作者、年代、内容等方面真伪的考辨。倘若误将真书作为伪书而弃之不用,那实为损失。在疑古过度的情况下,许多古籍如《鹖冠子》《文子》被疑为伪书,后经出土文献证实一批古籍是可信的。倘若误将伪书作为真书看待,那必有贻害。例如,1961年至1962年间,新疆博物馆两工作人员合谋,利用13世纪的旧文书(真文物)上书写伪造的所谓唐代的《坎曼尔诗笺》,曾轰动一时,那时举凡涉及唐诗、民族文学之典籍,几乎无一不予以采纳,甚至还曾入选中小学课本,可知造成影响之巨大,而这件赝品产生极坏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郭沫若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前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辨伪学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意义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不辨别文献的真伪就无法确定该文献的价值;二是不辨别文献的真伪就无益于文献的整理工作;三是不辨别文献的真伪就无法认识学术源流;四是不辨别文献的真伪就不可能进行科学的学术研究。因此,对于读书治学来说,辨伪是一个首要的环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云:“”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
五、辑佚学之功用
辑佚学为治学提供阅读资料之基础。人类若失去了所有的文献,那就等于集体患上了失忆症,真的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然后又要到哪里去了?人类要“立言”,那就离不开文献。辑佚是从传世的有关文献中钩稽、辑录已经散佚的整部古书或现存古书中部分遗失的内容,前者称辑集,后者称辑补。清代皮锡瑞认为清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一曰辑佚书”“一曰精校勘”“一曰通小学”,而辑佚居其首,可见辑佚之重要。辑佚有四大意义:一是恢复旧典,这主要是辑集;二是完备资料,这主要是辑补;三是保存文献,这主要是依靠辑集或辑补传承文献;四是存目备考,这主要是汇集佚书目录,有利于了解文献流传或学术变迁。从某个角度来说,辑佚具有填补某种文献空白的作用,同时有利于治学,如鲁迅著述《中国小说史》之前,先辑编《古小说钩沉》。辑佚是繁复的搜集、甄辨、拼合、考证工作,有了辑佚就可能提供治学所需的文献,有利于学术研究与学术发展。
六、文化传承之功用
人类不断地返回传统,是为了在文化的源头体认民族文化的力量,感受生存的意义,看清发展的方向。古典文献学揭示传统知识的结构,描绘文献的传递过程和知识运动的轨迹,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文脉传承,古典文献学记录文献的文化价值甚至大于其文献自身价值。如“江南三阁,文澜独存”,文澜阁《四库全书》历经磨难,一批批有志之士不遗余力,甚至不惜舍生忘死,毁家纾难,护书有功。抗战期间,“阁书颠簸流离,奔徙数千里,其艰危亦远甚于往昔,八载深锢边陲,卒复完璧归杭”,这一文献收藏转移中体现的民族精神光照千古。
古文献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要全面搜集、科学甄辨和正确理解古文献,就必须依靠古典文献学。现在国学业已成显学,我们无论对于国学作何定义或对于国学作何理解,都不能离开传统文化这一核心内容。古文献学不仅属于国学,而且是国学的基础。因此,我们要了解与研究国学就必须学习古典文献学,随着国学的复兴,古典文献学也必将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学界现在提倡重建中国古典学,那是肯定离不开古典文献的。裘锡圭认为:“我们认为中国的‘古典学’,应该指对于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或许还应加上与先秦典籍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些汉代的书,如《史记》先秦部分、《淮南子》、《说苑》、《新序》、《黄帝内经》、《九章算术》等)的整理和研究,似乎也未尝不可以把‘古典学’的‘古典’就按字面理解为‘上古的典籍’。我们的古典学的涵盖面不必如西方的古典研究那样广。这是由先秦时代的语言和历史跟我们的关系所决定的。”古典文献学可以指导古籍的出版、收藏和交流,以至于出版家找到了可供印刷的书籍,收藏家找到了值得购置的资料,研究者找到了有用的文献。
综上所述,古典文献学的意义十分重大,不仅是读书治学之门径,也是古代学科之基础,而且还有利于促进现实的文化建设,并为经济社会提供有效的服务。
第三节 古典文献学的学习与研究方法
一、充分认识与了解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
任何一门学问的学习与研究都离不开正确的理论与方法作为指导,古典文献学的发生与发展同样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而且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成熟的研究方法,如历史研究法、考据法、分类法、案例法、比较法、统计法、分析法,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该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并了解该门学科的研究方法。
二、广泛阅览,增加阅读体验
古典文献学是以古文献为研究对象的,那么我们要掌握这门学问,就应该对于古文献有更多地认识与了解,否则该门学问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大量阅览古文献,才会熟知古文献的内容;大量过眼古籍,才会对于古籍的装帧形式及其历史感有深切体会。阅读是一种资历,也是一种体验,“阅读意味着接近一些将会存在的东西”。书籍有历史,阅读也有历史,这两者的历史可以反映人类文明的进程。曾有人如此讴歌:“阅读之于思想,正如音乐之于心灵。阅读给人以激励,给人以力量,使人陶醉,使人充实。白纸上、电脑屏幕上的那些小小的黑色符号,让我们感动而泣,让我们开启新生活,感受新观念、新见解,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启迪,让我们的生存井然有序,把我们与世间的万物相连。毫无疑问,世间最神奇的事莫过于阅读。”为了学习与研究古典文献学,我们就需要广泛地阅读古籍、触摸古籍。
三、积极参与古文献整理工作
理论应该密切联系实际。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甚至凸显出其非常强的工具性。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也是从古籍整理的实践中总结出的成果,其方法也是通过古籍整理实践有效的检验。因此,我们为了更好地学习与研究古典文献学,就必须积极参与古文献整理工作,获得古籍整理的直接经验,并及时总结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如此则会更有效地掌握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更为透彻地理解这门学科。
四、借鉴相邻学科的成果
古典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与许多学科相互关联,只有借鉴相邻学科的最新成果,才能助益该学科的发展。只有借鉴考古学的成果,古典文献学才能完善与发展其出土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否则无从谈起。只有借鉴信息科学的成果,古典文献学才能跟上时代发展潮流实现古籍数字化,建立电子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只有借鉴语言文字学的成果,才能有助于提高文字、音韵、训诂学的水平。因此,及时吸收并借鉴相邻学科的成果,古典文献学学科才会与时俱进。
学习、研究与发展古典文献学是我们肩负的责任,任重而道远。倘若我们不能够保存和利用我国丰富的文献典籍,那么我们将有愧于我们的祖先,也有负于未来。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应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倘若从本学科做起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打造高水平的古典文献学的学科,提高古籍整理的水平。
编辑:赵露晴 初审:刘雯 复审:俞林波 终审:张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