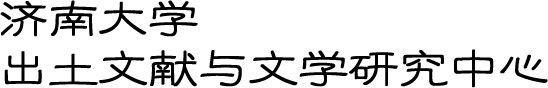凡例
一、释文来源。以整理者所释为底本,释文、断读参照时贤的新出研究成果,也有个人意见;引用学者的考释意见在注释中予以帮助或体现在参考文献中(已取得到学界公认的考释意见一般不注)。
二、例句录写。在不影响简文理解的情况下,基于文字输入和閲读顺畅的考虑,若非涉及必要字词,释文尽量从宽。引用的释文若有字词改动,于例句首引用处或必要处加以帮助;若有标点符号变动,不附帮助。合文、重文,一般直接写出,另“是=”“僞=”“营=”“数=”等少数合文或重文形式的训读存在不同意见,照录原文。存疑的隶定或释读字后加“?”。
( ),表示前一字是通假字、异体字或古今字;
< >,表示前一字是讹误字;
=,表示重文或合文;
□,表示简文模糊或残缺,无法补出的字;
〼,表示简文残损,残缺字字数无法确定;
底纹文字,表示据残笔参照文例补出的字;
【 】,表示简文原有残缺,可据文例补足的字;
〖 〗,表示简文原有脱文,可据文例补足的字;
{ },表示符号内的字为衍文。
……,表示简文节选而未全引或原简文字漫漶不可辨识。
三、来源标注。一般于例句后用下标形式标写“文献简称+简号”,简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简文若分栏书写,遵循原著录在简号后用“壹、贰、叁”等大写数字或“上、(中)、下”标示栏次。少数于期刊中公布的散见日书,例句后用下标形式标写“文献简称+文献来源”;若有简号,则一并标注。所引例句,若出自编号不同的简牍,为简文连贯之目的,将简号移至例句末标注:简号前后相连,简号间用“—”表示;简牍为研究者缀合,简号不相连属,简号间用“+”表示。整理者所编简号,经研究者重新缀连,采用研究者的标注方式,即据简文所处简的位置,在原简号后缀以A、B、C等字母。
日书例句出处与简称情况:
《九店楚简》《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 九店
《睡虎地秦墓竹简》《秦简牍合集〔壹〕》《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贰)》 睡
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 睡甲
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乙种 睡乙
《关沮秦汉墓简牍》《秦简牍合集〔叁〕》《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叁)》 周秦
《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 王
《天水放马滩秦简》《秦简牍合集〔肆〕》《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肆)》 放
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 放甲
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 放乙
《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书迹选粹》 北秦
《江陵岳山秦墓》《秦简牍合集〔叁〕》《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叁)》 岳山
《敦煌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 敦煌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居延汉简补编》 居汉
《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居延新简释校》《居延新简集释》 居新
《额济纳汉简》《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 额
《汉简〈日书〉丛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 悬泉
《武威汉简》《汉简缀述》 武威
《阜阳双古堆汉简数术书简论》《阜阳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编》 阜阳
《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概述》《介绍近年江陵张家山出土的西汉简书》 张M249
《虎溪山一号汉墓葬制及出土竹简的初步研究》《沅陵虎溪山汉简选》 虎
《西安杜陵汉牍〈日书〉“农事篇”考辨》 杜陵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 港
《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 孔
《印台墓地出土大批西汉简牍》 印台
《肩水金关汉简〔壹〕》《肩水金关汉简〔贰〕》《肩水金关汉简〔叁〕》 金关
《水泉子汉简初识》 水
《北大汉简——填补历史空白的佚本》《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书迹选粹》 北汉
《湖北随州市周家寨墓地M8发掘简报》 周汉
绪论
日书文献保留了弥足珍贵的文学资料,如首次出土的日书——睡虎地秦简日书,保留了牛郎织女传说的早期形式,有禹娶涂山氏的记录,有志怪色彩浓厚的长篇《诘》,有全篇押韵、行文流畅的祝祷辞《马禖》等,亦有局部押韵之文,如《取妻出女》篇简8背贰—9背贰:“月生五日曰杵,九日曰举,十二日曰见莫取,十四日奊(謑)訽,十五日曰臣代主。代主及奊(謑)訽,不可取妻。”再如汉代重要日书——孔家坡汉墓竹简日书简文有神话传说人物西王母、蚩尤等,有“河汉”隔绝之描写,有文学色彩较强的全篇或局部押韵之文,全篇押韵之文见各词条,局部押韵之文如《辰》篇“正阳”条:“正阳,是胃(谓)番昌,小事果成,大事有庆,它事未小大尽吉。利以爲啬夫,三昌。□时以战,命胃(谓)三34胜。以祠,吉。以有爲也,美恶自成。生子,吉。可以葬。以雨,齐(霁)。亡者,不得。正月以朔,岁美毋(无)兵。35”再如“徼”条:“不可以取(娶)妻、嫁女、出38入畜生(牲)、爲啬夫、临官、酓(饮)食、歌乐、祠祀、见人,若以之,有小丧,毋(无)央(殃)。以生子,子死,不产。取(娶)妻、嫁女,两寡相当。39”再如《占》篇简414:“正月戊己有北风,发(废)屋折木,命曰飢(饑)。小人卖子,君子卖衣;君子忧,小人流。”
“中华简帛文学文献集成及综合研究”中的综合研究涉及简帛文学的体裁、特点,文学现象的源起,文学专题研究等、语言研究等内容。语言研究对于文学现象源流的判定、文学专题讨论的深化有推动作用。
简帛文献的成书、出土地域一般而言较为明确,但也争议者。如糅秦楚于睡虎地秦简日书文献各篇章的地域归属、放马滩秦简《丹》篇的成书时代等。对简牍日书文献进行语言研究,可以为日书文献成书时代、地域归属提供鉴别依据,进而促进简帛日书文献文学的地域演变研究。
词汇是语言中最敏感的要素,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简帛日书文献词汇研究”以日书文献为研究对象,在梳理日书特色词汇的基础上,开展简牍词汇一般现象研究。即通过汇释日书数术术语,减少日书文献的阅读障碍;通过清理日书同义词,展现日书文献同义词的分布状况并着力探求秦汉时期同义词的复音发展演变与常用词替换现象;通过比较日书历时异文,揭示日书文献语言随时变化的特点;通过汇集日书文献中对大型辞书有修正作用的词汇词义,透视日书文献语言研究的应用价值。这些研究对于文学文献的流变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如根据篇章所使用的方言词汇,可以对杂有秦除日书的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属于文学研究的重要关注篇章《诘》篇的楚地归属作出推断,该篇使用了较多楚地方言,其反映的当是楚文学特征。
一、“日书”的界定
“日书”一词,包括日书这种古书类型,传世文献均未见,为考古新发现。“日书”书题首见于睡简。睡虎地M77汉简,北大西汉竹书、胡家草场汉简也发现了自题为“日书”的文献;此外,孔简有疑似“日书”书题。截至目前,已知自题为“日书”的简牍共计4批,疑似1批。
秦汉时期“乃一鬼神数术之世界”,《汉书·艺文志》“六略”中有数术略,选择时日或占测时日吉凶是数术略的重要内容,“《史记》有《日者列传》,《论衡》对当时的各种择日行为作过批判,足见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在战国秦汉时期早已十分流行。”百年来出土简牍有百余批30余万枚,简帛文献数量丰富,出土地域广泛,记载内容庞杂,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战国秦汉乃至魏晋时期的社会生活实景。反映战国秦汉时期择日习俗的简帛文献——《日书》也频见出土。
“日书”书题出土以前,西北汉简中已零星出土了日书类简牍,且因其内容特别受到关注,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部分单列“术数类”,《武威汉简》将这类简牍归入“日忌杂占”。不过类别特征明显、数量庞大的西北大宗屯戍简牍中的日书类简牍终因子量少,内容单薄,在流行广、影响大的简牍整理研究资料中杂于其他简牍中而未能单列成类。
“日书”书题出土以后,日书类简牍多有发现,但直至2006年睡虎地汉简、2009年北大西汉竹书中才又复见“日书”书题,所以在此期间或之后出土的数量众多的其他日书类简牍的命名与归类整理,是研究者据简牍内容,经与睡简《日书》或传世选择类通书对照而确定的。各批次简牍的发掘报告或资料公布、整理成果中自称有日书文献的简牍依时间先后排列有:1睡虎地秦简(1976)、2定县汉简(1981)、3花果山汉简(1982)、4阜阳汉简(1983)、5九店楚简(1984)、6张家山M249汉简(1985)、7放马滩秦简(1989)、8张家山M327汉简(1992)、9王家台秦简(1995)、10尹湾汉简(1996)、11悬泉汉简(1998)、12周家台秦简(1999)、13岳山秦牍(2000)、14马王堆帛书(2000)、15孔家坡汉简(2000)、16香港中文大学汉简(2001)、17杜陵汉牍(2002)、18虎溪山汉简(2003)、19上博简(2004)、20岳麓秦简(2008)、21睡虎地M77汉简(2008)、22印台汉简(2009)、23水泉子汉简(2009)、24北大汉简(2009)、25北大秦简(2010)、26浙大楚简(2011)、27周家寨汉简(2014)、28夏家台楚简(2016)。
随着对日书认识的深入,研究者发现1976年以前出土的西北屯戍简牍如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以文献简为主的武威汉简等简牍中,也散见有日书内容,并开展了释文解读或资料整理工作。
日书文献虽然先秦已然存在,但近年才始露面目,是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文献形式。研究者对其细节的界定存在不同。现将研究者的观点罗列如下:
饶宗颐:“日书者,当是日者所用以占候时日宜忌之书。”
睡简整理者:“《日书》的主要内容是选择时日,……其它如房屋的布局、井、仓、门等应该安排在什么地方才会吉利,遇到了鬼怪如何应付等等,也是重要内容。”
郑刚:对日书的理解有两个层次,其表层是其实用目的,是择日之术;而其深层则是择日的原理。日书不完全是按日排列的择日术,择日之术有完全不同的来源,日书的吉凶判断不全是择日,还有形法,根据表层确定其性质极为危险。
蒲慕州:日书是日者所用的占测时日之书,不过《日书》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书”,而是一些个别篇章的集结。
李零:日书是古代择日书的一种,把各种举事宜忌按历日排列,令人开卷即得,吉凶立见,即使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也很容易掌握,这种书在古代很流行,从战国秦汉一直到明清,传统从未断绝,在民间影响更大,是早期的“黄历”。日书讲吉凶宜忌,一定要具体到日,专门讲日,才叫“日书”。现存日书,“除选择时日,还旁及星占、式法、风角、五音、纳甲、十二声、六吕六律、卜筮、占梦、相宅,以及厌劾祠禳,它还试图打通各类数术”,日书的选择事项,简直无所不包,凡是日常生活可能涉及的方面,都可以装进这个体系,它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不光讲时间,也讲空间。“日书是类名,不是专名”。
刘乐贤:《日书》是古代数术学中的择日类书籍,是古代选择通书,“《日书》的内容首先可以分为择日部分和非择日部分。择日部分是《日书》的主体,非择日部分则是一些附属材料。”《日书》以选择或占测时日吉凶为主,还包括一些别的涉及日常活动的数术方法,具有杂抄或汇编当时各种日常趋吉避凶方法的倾向,与后世流行的选择通书性质相近。
曾宪通:日书本是古代日者用来占候时日宜忌、预测人事休咎、以教人如何避凶趋吉的历书,带有相当浓厚的数术色彩。
工藤元男:《日书》是“以占卜为职业的日者所用的书籍。”
胡平生:“《日书》是查询岁月时日的吉凶宜忌之书,较利用龟甲、蓍草、式盘等各种占卜器具都来得简便明了,似为秦汉时民间流行的指导日常行为的工具书。”
吴小强:专司卜测时日吉凶的日者所使用的工具书即《日书》,“《日书》是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社会中下阶层的一种日常生活生产手册,主要用于推择时日、卜断吉凶,从而使人们达到趋吉避忌、得福免灾的目的。”
王子今:“《日书》是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
何双全:《日书》按字义理解,就是有关选择日子的书,有点像现在流行的老黄历;但比老黄历要复杂得多,《日书》应是老黄历的始祖。古人选日子的概念商周甲骨文中已有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且渐有体系,《日书》就是物证。战国至秦,又有了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员“日者”。
晏昌贵:《日书》是古代日者选择时日、占断吉凶的实用手册,类似现今仍在港台地区民间流行的通书或黄历;《日书》文本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以天文历法为经,以生活事件为纬;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观察,《日书》以“时”序“事”,将人事附着于天文,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其占卜的内容,可以用“生老病死,衣食居行”八个字来概括。
吕亚虎:《日书》流行于社会中下层,是一种便捷的,与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术数手册;主要用于推择时日、占断吉凶,从而使人们达到趋吉避凶、求福免灾的目的。
孙占宇:“日书为日者所操之工具书,这是学界的一致看法。……日者‘占候卜筮’的对象其实十分广泛,非仅时日吉凶。……秦汉时期‘日书’是一个较为宽广的概念,凡与百姓生活相关的占卜术、厌禳术、祝由术及其他数术皆可归入其中,若仅从字面上将‘日书’理解为择日之书,恐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秦汉时期‘日书’与后世流行的选择通书性质相近,凡与人们生活相关的占卜术、厌禳术、祝由术及其他数术皆可归入其中,并不局限于字面意义上的‘择日之书’。”
以上诸家将日书或理解为择日之书,或理解为日者所用择日之书,或理解为择日为主的数术杂抄。由于对日书的所指理解不同,各家认定的日书文献也有差异。现以时间为序,将部分研究者认定的日书文献列表如下:
| 李1993 | 胡 1995 | 工1998 | 何1998 | 陈 2001 | 刘2003 | 李 2004 | 晏 2006 | 森2008 | 吕 2010 | 李 2011 | 晏 2011 | 黄2013 | 大2014 | 骈2015 | 合计 |
睡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
定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1 |
阜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1 |
九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
张M24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
放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
张M32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王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
尹湾 |
|
|
| + |
|
|
| (+) |
|
|
| (+) | + |
|
| 2+2 |
周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岳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马王堆 |
|
|
|
|
|
|
| (+) |
|
|
| (+) | + |
|
| 1+2 |
孔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
港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 |
杜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虎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1 |
上博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睡汉 |
|
|
|
|
|
|
|
|
|
| + | + | + | + |
| 4 |
印台 |
|
|
|
|
|
|
|
|
|
| + | + | + | + |
| 4 |
水简 |
|
|
|
|
|
|
|
|
|
| + | + | + | + |
| 3 |
北汉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北秦 |
|
|
|
|
|
|
|
|
|
| + |
| + | + | + | 3 |
浙楚 |
|
|
|
|
|
|
|
|
|
|
|
| + | + |
| 2 |
敦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
居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 |
武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1 |
悬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银雀山 |
|
|
| + |
|
|
| (+) |
|
|
|
| + |
|
| 2+1 |
合计 | 7 | 8 | 9 | 12 | 10 | 16 | 13+1 | 8+9 | 18 | 15 | 22 | 22+2 | 28 | 24 | 16 | 28 |
可以看出,学界对上博、浙楚、岳麓、银雀山、马王堆、花果山、尹湾这几批简帛材料有日书文献的认可度不高。不过,即便是认可度较高的日书文献,其中的某些篇章,也有研究者将其与日书区别开来,如睡简中的《诘》《梦》《相宅》《置室门》,放简中的音律贞卜内容,九店中的《告武夷》《相宅》,孔简中的《岁》等;也有研究者将整理者未认定为日书文献的某些篇章归入日书,如放简中的志怪故事,周秦中的历谱等。
日书的最大特点是实用性,它经常与实用性简帛文献一起出土;除此之外就是简便性,是日常生活中趋吉避凶的便捷手册。每日行事是日常生活的主体内容,而每日行事宜忌便构成了日书的主体。日者是日书的专职使用者,日者被称为日者不是因为其使用日书,而是因为其职责是占日(以时索事,为事择时),但日书不独为日者所用。日书经历了庞杂到纯粹的发展过程,睡简日乙119有“凡戊子风,有兴。雨阴,有疾。兴在外,风,军归”,放简日乙346有“邦居军:丙丁畾(雷),军后徙;戊己畾(雷),军敬(警);庚辛畾(雷),军前徙,为雨不徙;壬癸纍<畾>(雷),战”,104壹有“乘马到邑,止不肎(肯)行者,以毂中脂入其口中”,122有“大虻音曰鼠德日以衰其室空虚取土地以连之得财及肉□□有邑殹”等内容;早期日书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无关日常生活的非择日内容。
本选题的研究目的是讨论简帛日书的语言特点,日书、阴阳、形法等相关数术文献的语言特点基本一致,某些被整理者辑入日书的简文是否被剥离出去,对研究结果应不会造成太大影响。本研究对于日书语料的认定遵从通行观点,排除未公布的定县汉简、张家山M327汉简、睡虎地M77汉简、夏家台楚简这4批日书,纳入本研究范围的日书语料是:
敦煌、居汉、武威、居新、金关、睡简、阜阳、九店、张M249、放简、岳山、港简、悬泉、王简、周秦、额简、虎简、孔简、杜陵、印台、水简、北汉、北秦、周汉,共计24批(文末附包括港简、武威在内的散见简帛日书释文以便查閲)。
二、简帛日书语料介绍
日书简帛材料丰富,纳入本课题研究范围的共有24批材料。下面是各批日书文献基本情况的介绍。
(一)敦煌汉简
1906年至1988年,甘肃西部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烽燧遗址共发掘出土了8批2484枚简牍,被称为“敦煌汉简”。《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敦煌汉简释文》收录了这批简牍的释文,《敦煌汉简》图版、释文均有收录,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通用版本,《中国简牍集成》收录了这批简牍的释文,有断句和简单注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公布了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1906—1908)所获为主的2842枚残简。新近出版的《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提供了“原简原色原大”的彩色图版和红外扫描图版,利用红外线辨识简牍字迹,吸收学界研究成果,修正完善了释文,是敦煌汉简研究的最新成果和集成之作。
敦煌汉简以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期居多,纪年简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最晚的是东汉桓帝元嘉二年(152);简文以屯戍行政文书为主,还有小学、数术、方技等文献,其中日书简有24枚。何双全、罗帅、陆平、张志杰等先生对其中的日书简做过整理研究。
(二)居延汉简
1930年10月至1931年5月,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汉代居延烽燧遗址出土了12000余枚简牍,被称为“居延汉简”。这批简牍的释文整理考释版本较多,其中谢桂华等先生合编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逐一校释以往诸家释文,吸取当时学界的研究成果,大大提高了释文的准确性,是研究居延汉简的通用版本。《中国简牍集成》收录了这批简牍的释文,有断句和简单注释。《居延汉简补编》利用红外影像技术,辨识模糊图版或“无字简”,增补未刊布简牍。2012年底至今,台湾史语所重新扫描这批收藏于史语所的居延汉简,并参校各版本,吸收学者的校改成果进而整理作出释文,预计出版四到五册,目前已经出版了四册。
居延汉简以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期居多,纪年简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最晚的是东汉和帝永元十年(98);简文主要是屯戍行政文书,日书简仅有1枚。何双全、罗帅、陆平、常燕娜等先生对其中的日书简做过搜集研究。
(三)武威汉简
1959年7月,甘肃武威磨咀子M6汉墓出土了469枚竹木简;同年秋天,M18汉墓又发现了10枚“王杖”木简;此外,M15、M22、M23号汉墓又有柩铭出土。这些在武威磨咀子出土的竹木简和柩铭被统称“武威汉简”。《武威汉简》收录了这批简牍的图版、释文,《汉简缀述》对其中的日忌简进行了考证,《中国简牍集成》收录了这批简牍的释文,有断句和简单注释。
磨咀子M6汉墓出土有日书简,其中一枚简背记有“河平□年四月四日”,整理者据此推断这批日书当是西汉晚期之物;武威汉简以三个《仪礼》写本为主,日忌杂占简有11枚。
(四)居延新简
1972年秋至1976年夏秋,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汉代居延甲渠候官、第四燧、金关烽燧遗址出土了19700余枚简牍;其中甲渠候官(破城子)和甲渠塞第四燧出土的8000余枚简牍整理较早,为了与居延汉简区分,被称为“居延新简”。《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公布了这批简牍的释文,《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图版、释文均有收录,又补充了1976—1986在居延地区复查时发现的简牍释文及图版,是研究居延新简的通用版本。《中国简牍集成》收录了这批简牍的释文,有断句和简单注释。新近出版的《居延新简释校》以原简的简影图版为据,对这批简牍的不同释文版本进行合校,改正了原整理本的错字,增添了部分新释出字,完善了原有释文;《居延新简集释》采用红外线扫描技术,发表了清晰的红外线扫描图片,吸收学界研究成果,对释文进行了校正、补充,为学界提供了更为理想的读本。
居延新简以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期居多,纪年简最早的是西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最晚的是东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另有1枚西晋太康四年纪年简;简文主要是屯戍行政文书,日书简有31枚。胡文辉、刘昭瑞、何双全、魏德胜、罗帅、陆平、孙占宇、常燕娜等先生对其中的日书简做过搜集研究。
(五)金关汉简
1972年至1974年,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居延金关烽燧遗址出土了11000余枚简牍。目前金关汉简已整理完毕,共出版《肩水金关汉简》5辑。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仅整理了前3辑中的日书简,另外两辑若有日书语料,我们将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补足。
金关汉简以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期居多,纪年简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最晚的是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28)。简文主要是屯戍行政文书,前3辑中日书简有30枚。何双全、方勇、高一致、程少轩、刘娇、姚磊等先生整理研究过其中的日书简。
(六)睡虎地秦简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M11秦墓出土了1100余枚秦简,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日书》乙种共10种文献,引发学界广泛关注。日书简牍的整理发布稍晚于法律简牍,《云梦睡虎地秦墓》最早公布了这批日书文献的图版和初步整理的释文,图版采用连续排号方式,释文未加句读和注释;《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简牍篇》据《云梦睡虎地秦墓》对这批日书进行了标点和注解,精装本《睡虎地秦墓竹简》对图版重新编号,吸收学界研究成果,重新修订释文,标点断句,附入注释,是研究睡虎地秦简的通用版本。《秦简牍合集〔壹〕》收录了这批简牍的图版、释文,利用红外影像技术,获取了高质量的图版,对释文进行了补正、编连等工作,是这批简帛文献的“善本”;之后又出版了释文注释修订本,对释文、注释中已发现的问题作了最必要的修订。
睡虎地秦墓的下葬年代是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墓主喜是下层官吏。李学勤先生以秦铭文字体的演变为标尺,推断睡简的写成不早于秦昭王晚年;刘乐贤先生据《日书》不避秦始皇讳,推测《日书》的写成年代在秦王政即位(前246)之前,具体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246年之间或略前;陈伟先生据“正月”避讳情况,认为睡简日书大概是墓主喜成年以后收集或者抄写,其下限,因为未出现“黔首”一词,可以卡定在秦始皇25年,而早到昭王时代的可能性恐怕并不太大。睡虎地秦墓出土有《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等10种文献,以法律和日书文献为主;日书有甲乙两种,甲种简166枚,乙种简259枚,共计425枚。
(七)阜阳汉简
1977年7月至8月,安徽阜阳双古堆M1汉墓出土了1000余枚竹木简,3方木牍。这批简残缺严重,目前尚未全部公布;仅在论著中公布了部分图版、释文和注释。
阜阳汉墓的下葬年代是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墓主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竈。阜阳汉简内容丰富,有《苍颉篇》《诗经》《周易》《大事记》《万物》《作务员程》《行气》《相狗经》《刑德》《日书》《干支表》《向》《五星》《星占》及辞赋等十多种古籍残篇。日书简有近百个残片,近似于睡简日书乙种简117—128,“书中涉及的事项和人物则有‘产子’、‘啬夫升迁’、‘大将’、‘徙家’、‘得地’、‘取(娶)妇’、‘筑室’、‘蜚冬( )’、‘父母疾病’、‘少子’、‘中子’、‘长子’、‘土事’、‘讼’等等。从残存的近百片碎简已无法窥见此书原貌了。”已公布的日书简有15枚。
)’、‘父母疾病’、‘少子’、‘中子’、‘长子’、‘土事’、‘讼’等等。从残存的近百片碎简已无法窥见此书原貌了。”已公布的日书简有15枚。
(八)九店楚简
1981年5月至1989年底,湖北江陵九店M56楚墓出土了146枚有字简。《江陵九店东周墓》首次公布了九店楚简的图版、释文,《九店楚简》亦录有这批竹简的图版、释文,对释文进行了重新编连和释读,是研究九店楚简的通用版本。《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九店56号墓简册》利用红外线拍摄图片,吸收学界研究成果,修正了释文和注释。
九店楚墓的下葬年代应在战国晩期早段,墓主身份为“庶人”。竹简内容分为15组:第1组12枚简记载了农作物的数量,其性质有待研究;第2—14组共87枚简是日书简;第15组47枚简为残篇,内容多属日书。纳入本选题研究范围的日书简是较完整的87枚竹简。
(九)张家山M249汉简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湖北江陵张家山M247、M249、M258三座汉墓出土了1600余枚竹简,其中M249有日书简。目前这批竹简仅公布了部分图版和释文,全部材料尚未公布。
张家山三座汉墓的下葬年代,整理者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特点和墓葬竹简,判断上限为西汉初年,下限不会晚于景帝;M247出土《历谱》和律令,据其书写年代,该墓墓主应死于吕后二年,M249与M247的同类器物形制相同、墓坑相邻,墓葬年代当相同。M247出土竹简1200余枚,有《遣册》《历谱》《脉书》《引书》《算数书》《盖庐》《奏谳书》《律令二十六种》8种文献;M249出土竹简400余枚,其主要内容为《日书》;M258出土竹简58枚,内容为《历谱》。M249所出日书保存较差,出土时已散乱,整理难度大,仅在期刊论文中公布了8枚日书简照片。
(一〇)放马滩秦简
1986年6月至9月,甘肃天水放马滩M1墓出土了461枚竹简,4方木牍。这批简牍整理公布过程较长,自1988年、1989年起即有部分简牍图片、释文陆续公布,至2009年出版《天水放马滩秦简》,这批材料的图版和释文得以全部公布,为了解这批简牍的全貌进而开展系统深入研究提供了资料;但因竹简残缺、照片质量不高等原因,整理者对竹简的释读、缀合、编连不太理想,所公布的图版也不够清晰。《中国简牍集成》收录了日书甲种的释文,有断句和简单注释。《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提供了红外影像图片,对释文进行了断句、修订、缀合、编连等工作,是集中整理研究这批简牍的新作品。《秦简牍合集〔肆〕》收录了这批简牍的图版、释文,利用红外影像技术,获取了高质量的图版,并对释文进行了补正、断句、析分、缀合、编连等工作,是这批简帛文献的“善本”;之后又出版了释文注释修订本,对释文、注释中已发现的问题作了最必要的修订。
放马滩M1墓的墓葬时代,意见不一:整理者认为应“早至战国中期,晚至秦始皇统一前”,约在公元前239年以后;也有研究者认为放马滩秦简抄写于秦统一之后,“不能完全排除晚至汉初属于‘汉简’的可能性”。我们采用了竹简写成于秦代的观点。放马滩秦简的内容是日书和志怪故事(最初称作“墓主记”,研究者多主张称作“丹”),日书有甲乙两种,整理者认定的日书甲种竹简有73枚,日书乙种竹简有381枚。被整理者归入《志怪故事》的7枚简中,第6号简应归入日书乙种,可能和简342—344号这几枚简编联,孙占宇先生将该简归入日书乙种的《日辰星》篇或《阴阳钟》篇。综之,日书乙种竹简为382枚,放马滩秦简日书简共计455枚。
(一一)岳山秦牍
1986年9月至10月,湖北江陵岳山M36秦墓出土了两方木牍,均正背两面书写。《江陵岳山秦汉墓》公布了这两方木牍的释文和正面图版,新近出版的《秦简牍合集〔叁〕》收录了岳山木牍的图版、释文,提供了红外影像图版,对释文进行了修正、分篇等工作,是岳山秦牍的“善本”;之后又出版了释文注释修订本,对释文、注释中已发现的问题作了最必要的修订。
江陵岳山M36秦墓的下葬年代,整理者据墓葬器物组合形式、器形特征,判断应在秦统一以前或秦统一之初,与睡虎地秦简时代大体接近;墓主是秦国的中下层官吏。
(一二)港中大汉简
1989年至1994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入藏了259枚战国汉晋简牍,其中残片8枚,空白简11枚,楚简10枚,汉简229枚,晋牍1方。《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公布了这批简牍的图版、释文,并附有分类整理和详细考证,是研究这批简牍的通用版本。
港中大汉简日书的写成时代,整理者据简17有“孝惠三年”明确纪年,避秦始皇“政”讳,文字与马王堆简帛及银雀山汉简的字形基本相同,内容多可与孔简日书对读,判断这批日书简抄写于孝惠三年(前192)之后的汉初,出土地可能在湖北随州一带。同时又据这批日书内容大多可与睡简日书对应,避秦始皇“政”字讳,判断这批日书出土地可能原属秦地,或者说其祖本源自秦地。港中大汉简内容丰富,有日书、遣册、奴婢仓廪出入簿、序宁简、河堤简、解除木牍等,整理者将简11至119共109枚简归入“日书”;其中简95至119为干支表,未载择日行事宜忌,不属于日书内容。陆平先生又指出简77写有“元年□”,与《日书》无关,港中大汉简日书零简有83枚;刘乐贤先生认为“第40号简的内容也与《日书》相距甚远。”纳入本选题研究范围的日书简是简11至简94,排除简40和简77,共有82枚。
(一三)悬泉汉简
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了35000余枚简牍,有字简23000余枚,此外还有帛书、纸文书、墙壁题记等重要文物;经整理、编号、释文后约有17800余枚,这批简牍目前尚未完全发表,仅在论著中公布了部分图版和释文。
悬泉汉简以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居多,1900余枚简牍有明确纪年年号,纪年最早是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最晚是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简文有15类近百种,主要是簿籍、司法爰书、邮书等屯戍行政文书,还有日书、历谱、医方、相马经、葬书、《急就章》、《苍颉篇》、《论语》等;日书简为为残册断简,“大都残损,又无简题,难以复原”。《汉简〈日书〉丛释》公布了《日忌》《吉凶》《大小时》《建除》《禹须臾》《葬历》6类20枚日书释文。《敦煌悬泉汉简释粹》将悬泉汉简中《建除》《死》的部分日书内容分别编号为二五一、二五二,归入“典籍文化类”,作了注释,该书中编号为二六三至二六九的简牍亦当为日书文献。目前已公布的日书简有21枚,主要出土于第三堆积层,为西汉晚期之物。
(一四)王家台秦简
1993年3月,湖北江陵王家台M15秦墓出土了800余枚竹简,1方竹牍;竹简分为8组,共计813个编号。竹简保存情况较差,原貌已遭破坏。这批竹简尚未有全部材料的整理成果出版,仅在期刊论文中公布了部分图版和释文。
王家台秦墓的下葬年代,整理者据出土器物、竹简内容,推测墓葬相对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下限不晚于秦代。竹简主要内容是效律、日书和易占,日书数量最多,目前已公布的日书简有49枚。
(一五)周家台秦简
1993年6月,湖北荆州周家台M30秦墓出土了389枚竹简,1方木牍;竹简经拼缀,共有381个编号。《关沮秦汉墓简牍》公布了这批简牍的图版、释文和注释,是研究这批简牍的通用版本。《秦简牍合集〔叁〕》收录了这批简牍的图版、释文:图版采用整理者的照片为主,辅以少量红外影像;对释文、注释进行了补正工作,是这批简帛文献的“善本”;之后又出版了释文注释修订本,对释文、注释中已发现的问题作了最必要的修订。
周家台M30秦墓的下葬年代,整理者据出土简牍的纪年、墓主的死亡年龄,并参考避秦始皇讳(改“正月”为“端月”)、文字形体特征、随葬物特征,推测墓葬时间略晚于睡虎地M11秦墓,应在秦代末年,“其年代的上限与下限之间跨度较小”;结合墓葬中随葬器物的某些风格来看,也不能绝对排除墓葬下限晚至西汉初年的可能性。墓主可能是负责赋税收缴工作的佐史一类的南郡官署属吏。简文有历谱、日书、病方及其他,以日书为主,整理者将编号为131至308的178枚简(含空白简10枚)归入日书文献,被归入“病方及其他”的简355至363、简371共10枚简也应是日书内容。纳入本选题研究范围的日书简有188枚。
(一六)额济纳汉简
1999年9月至2002年10月,内蒙古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了500余枚汉简,被称为“额济纳汉简”,这是额济纳河流域继居延汉简、居延新简之后第三次发现的汉简。《额济纳汉简》收录了这批简牍的图版、释文,是研究这批简牍的通用版本。《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对释文作了校正,以加按语的形式指明所录释文与整理者的不同之处。
额济纳汉简以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者居多,纪年最早的是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前59),最晚的是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28),也有少量东汉中期简。简文主要是屯戍行政文书,也有《晏子》、《田章》、《苍颉》、医方、日书等残简;刘乐贤、陆平、常燕娜等先生对其中的日书简做过搜集研究工作。纳入本选题研究范围的日书简有9枚。
(一七)虎溪山汉简
1999年6月至9月,湖南沅陵虎溪山M1汉墓出土了1336枚(段)竹简,原有完整简约800枚。这批竹简尚未有全部材料的整理成果出版,仅有几篇论文公布了部分图版和释文。
虎溪山汉墓的下葬年代是西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墓主人是第一代沅陵侯吴阳。这批竹简的发掘报告中将竹简按内容分为黄簿、日书和美食方三类,其中日书简共1095枚(段),整简约500枚,是竹简的绝大部分;《阎氏五胜》(也作《阎氏五生》)为自署篇名,“有别于已出《日书》简的特点是为证明其推演的正确而引入秦末汉初的一些历史事件。”研究者对《阎氏五胜》篇的性质有不同意见,如刘乐贤先生指出“《阎氏五胜》虽然是从讲五行相胜开始,但其着重点明显落在要顺时举事的结论上。显然,这是一篇观点鲜明的论述性文字。发掘报告将其归入《日书》,似可商榷。《日书》一类文献,在战国秦汉墓葬和遗址中多有发现。其特点是只讲趋吉避凶之术,基本上不涉及价值判断,从中很难看出编写者的思想倾向。将它们和观点鲜明的《阎氏五胜》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具有明显区别,不宜归为一类。”“将《阎氏五胜》归入阴阳家似更为合适一些。”晏昌贵先生也认为《阎氏五胜》在性质上属于阴阳家文献,与“五行”类的《日书》并不完全相同;这就提醒我们注意,这批整简约500枚的所谓《日书》,可能大部分并不属于《日书》。本选题研究未含《阎氏五胜》篇,纳入研究范围的是已公布的与时日吉凶有关的5枚简。
(一八)孔家坡汉简
2000年3月,湖北随州孔家坡M8汉墓出土了700余枚竹简,4方木牍;其中一方告地书木牍有“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纪年。《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公布了这批竹简的图版、释文和注释,是研究这批简牍的通用版本。
孔家坡M8汉墓的下葬年代,整理者据该墓所出历日木牍,推断是西汉景帝后元二年(前142);也有研究者有不同意见,如陈炫玮先生据墓葬同出《历日》《告地书》及日书不避不避汉惠帝讳,推论《日书》抄本写成的年代下限当为汉高祖十二年(前195)。简文有日书、历日、告地书,其中日书简从内容看原应为一册竹简,但保存较差,部分简已失去原有编次。清理时共有703个编号,经整理者整理、缀连后有478个编号,另有残简48片;某些简号、某些残片也可以重新编连、缀合。
(一九)杜陵汉牍
2001年,陕西西安杜陵M5汉墓出土了1方木椟,单面书写。《西安杜陵汉牍〈日书〉“农事篇”考辨》公布了这方木牍的图版、释文,并有考证。《中国简牍集成》收录了这一木牍的释文,有断句和简单注释。
杜陵木牍所出汉墓地处汉宣帝刘询杜陵陵区,当属杜陵陪葬墓;木牍正面写有各种农作物种植的宜忌日,整理者将杜陵木牍拟名为《日书•农事篇》。
(二〇)印台汉简
2002年8月至2004年1月,印台9座汉墓出土了2300余枚竹木简,60余方木牍。这批简牍尚未有全部材料的整理成果出版,仅在期刊论文中公布了部分图版,刘乐贤先生对图版文字进行了隶释、考证。
郑忠华先生据墓葬出土的文书简纪年、编年记简所载编年、史实,推断印台汉墓的下葬年代是西汉景帝时期。简文内容分为文书、卒簿、历谱、编年记、日书、律令以及遣册、器籍、告地书等,日书内容与睡虎地秦墓所出有类似之处。这批简牍目前已公布的日书简有24枚。
(二一)水泉子汉简
2008年8月至10月,甘肃永昌水泉子M5汉墓出土了1400余枚(片)木简,木简出土时多残断,较为完整者有700多枚(片)。这批汉简尚未有全部材料的整理成果出版,仅在论著中公布了部分图版和释文。
水泉子M5汉墓的墓葬年代,整理者据墓葬形制,推测是西汉末至东汉早、中期;简文主要是日书和字书,日书字体是西汉末或东汉前期的通行字体。这批日书简目前已公布20枚。
(二二)北大汉简
2009年1月,北京大学获赠3346枚竹简,竹简保存情况良好,内容都属于古代的书籍,被称为“西汉竹书”。北大汉简计划出版七卷,目前已出版五卷,第一卷收录《苍颉篇》,第贰卷收录《老子》,第三卷收录《周驯》《赵正书》《儒家说丛》《阴阳家言》四种,第四卷收录《反淫》《妄稽》两种,第五卷收入《节》《雨书》《揕舆》《荆决》《六博》五种。第六卷包括三种“日书”类的数术书,第七卷包含180多种病方的医书,此二卷也将在两年内陆续推出。
北大汉简的抄写年代是西汉中期,内容丰富,包含17种古书,大致涵盖了今天的哲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医学等学科,是目前所见战国秦汉古书类竹简中数量最大、保存质量最好的一批。其中日书简有1000多枚,可谓此类文献中的集大成者。不过目前该批竹简中的日书简尚未出版,仅公布了《占盗》《人字图》篇的11枚简的图版和释文。
(二三)北大秦简
2010年初,北京大学获赠795枚简牍,包括竹简762枚(其中有近300枚为两面抄写)、木简21枚、木牍6枚、竹牍4枚、木觚1枚、竹简残片若干;这批简牍的拍照、编连与文字释读工作2012年已经完成,但尚未出版,仅在论著中公布了部分重要篇章的图版和释文,部分篇章有详细的考证论述。
北大秦简的书写年代,整理者据这批简牍大都用秦隶书写,有秦始皇三十一年和三十三年两组日历,“参考简牍内容,可判定抄写年代约在秦始皇时期或稍早。”简文内容丰富,有《从政之经》《善女子方》《公子从军》《道里书》《田书》《算书》《制衣》《白囊》《隐书》《禹九策》《祓除》《三十一年质日》《三十三年质日》《泰原有死者》、饮酒歌诗、日书甲乙组、医书、九九术、记账文书等,涉及古代政治、地理、数学、历法、民间信仰、文学、医学、方术等诸多领域;其中卷贰55枚简和卷肆中的小部分简属于日书简。目前公布的日书简有3枚。
(二四)周家寨汉简
2014年9月至11月,湖北随州周家寨M8汉墓出土了一批简牍,竹简编号有566个,完整竹简约360枚,另有《告地书》木牍1枚、签牌3支。这批简牍目前正在整理过程中,其发掘情况及时见诸报道,发掘报告也于近期得以发布,陆续有简牍图版、释文和考释性材料发表。
周家寨M8汉墓属于随州孔家坡汉墓群的组成部分,其下葬年代,据所出木牍纪年推断,是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或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墓中下葬品为江汉地区西汉早期墓葬常见的陶器组合形式,墓主身份为高里公乘;竹简的内容主要是日书,与孔简日书内容接近,年代相仿。目前已公布日书简图片51枚,其中文字清楚,能纳入本选题研究范围的有40枚简(44个简号,含残简2个)。
以上是各批日书基本情况介绍,竹简总计2065枚,木牍3方。日书文献内容丰富,抄写时间有跨度且前后连贯,出土地域有区别且地域交融;为诸多领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现列表呈现各批次日书的出土时间,所属时代、数量、著录情况。
序号 | 名称 | 出土时间 | 墓葬时代 | 主要著录情况 | 数量(枚/方) |
1 | 敦煌 | 1906—1988年 | 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后期 | 《敦煌汉简》《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 | 24 |
2 | 居汉 | 1930—1931年 | 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后期 |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 《居延汉简补编》(壹—肆) | 1 |
3 | 武威 | 1959年 | 西汉晚期 | 《武威汉简》 | 11 |
4 | 居新 | 1972—1982年 | 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后期 | 《居延新简——甲渠候官》 《居延新简集释》 | 31 |
5 | 金关 | 1972—1974年 | 西汉中后期至东汉 | 《肩水金关汉简》(壹—伍) | 30 |
6 | 睡简 | 1975—1976年 | 秦始皇30年 | 《睡虎地秦墓竹简》 《秦简牍合集〔壹〕》 | 日甲166 日乙259 |
7 | 阜阳 | 1977年 | 下限不晚于汉文帝十五年 | 《阜阳双古堆汉简数术书简论》《阜阳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编》 | 15 |
8 | 九店 | 1981—1989年 | 战国晚期早段 | 《九店楚简》 《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 | 87 |
9 | 张M249 | 1983—1984年 | 西汉初至汉景帝 | 《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 | 8 |
10 | 放简 | 1986年 | 秦代 | 《天水放马滩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秦简牍合集〔肆〕》 | 日甲73 日乙382 |
11 | 岳山 | 1986年 | 秦统一前或秦统一初 | 《江陵岳山秦汉墓》 《秦简牍合集〔叁〕》 | 2(方) |
12 | 港简 | 1989—1994年(购入) | 西汉惠帝三年后 |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 | 82 |
13 | 悬泉 | 1990—1992年 | 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 | 《汉简〈日书〉丛释》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 | 21 |
14 | 王简 | 1993年 | 白起拔郢至秦代 | 《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 《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 | 49 |
15 | 周秦 | 1993年 | 秦代末年 | 《关沮秦汉墓简牍》 《秦简牍合集〔叁〕》 | 188 |
16 | 额简 | 1998—2002年 | 西汉晚期至东汉中后期 | 《额济纳汉简》 《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 | 9 |
17 | 虎简 | 1999年 | 西汉文帝后元二年 | 《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虎溪山一号汉墓葬制及出土竹简的初步研究》《沅陵虎溪山汉简选》 | 5 |
18 | 孔简 | 2000年 | 西汉景帝时期 | 《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 | 526(含残48) |
19 | 杜陵 | 2001年 | 西汉宣帝时期 | 《西安杜陵汉牍〈日书〉“农事篇”考辨》 | 1(方) |
20 | 印台 | 2002—2004年 | 西汉景帝时期 | 《印台墓地出土大批西汉简牍》 《印台汉简〈日书〉初探》 | 24 |
21 | 水简 | 2008年 | 西汉末或东汉前 | 《甘肃永昌水泉子汉墓发掘简报》 《水泉子汉简初识》 | 20 |
22 | 北汉 | 2009年(获赠) | 西汉中期 | 《北大汉简——填补历史空白的佚本》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墨迹选粹》 | 11 |
23 | 北秦 | 2010年(获赠) | 秦始皇时期或稍早 | 《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书迹选粹》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 | 3 |
24 | 周汉 | 2014年 | 西汉武帝元光元年 | 《湖北随州市周家寨墓地M8发掘简报》 | 40 |
总计 | 竹木简2065枚,木牍3方 |
三、简帛日书研究现状
(一)简帛日书有较长时间的积累
简帛日书在20世纪初由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得以屯戍文书为主的709枚敦煌汉简中已零星出现,因这些简牍内容特点鲜明,早期整理时便被甄别出来,独立考释。法籍汉学家沙畹系统整理了斯坦因所得简牍,于1913年出版了《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该书将这批汉简中具有书籍性质的简牍,分为“占卜、医书和其他”三类,其中占卜简收列2枚。罗振玉、王国维是我国最早研究汉简的学者,他们据沙畹提供的初稿、图片对斯坦因所得汉简进行了释读和考证,于1914年出版了《流沙坠简》;该书依据内容将简牍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三类,其术数类中的“吉凶宜忌残简”小类收列5枚残简。由于此类简牍数量少,且残缺不成系统,罗氏虽明“右五简记吉凶宜忌”,但“其义不可尽晓”;在此艰难境况下,罗氏仍借助传世古籍的零星记载,对简文的数术词语如“大时”“小时”“月杀”等“随文加释”。陈槃先生也很早便开始从事西北汉简中日书等数术散简的集成工作,被称为“治谶纬之巨擘”。由此可见,在数量庞大的边塞文书中,日书简虽只是偶见;但其与屯戍文书区别明显,自简牍资料的整理释读起,便被甄别出来,独立考释。但是限于同类简牍数量稀少,内容单薄,可资对比的资料少,解读不易,全面深入研究受限,以至于当时的研究者不能形成对日书面貌的宏观认识;当时的日书资料更不足以支撑起一个研究方向或一个研究领域。
1975年睡简日书批量出土,是日书文献深入研究的发展契机。不过同墓出土的法律简牍数量巨大、内容完整,填补了传世文献秦律的缺失,尤其具有历史突破意义;再加上人力、物力等方面的限制,以及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睡简未能同时全部整理公布,法律简牍率先见诸国内重要报刊报道,如《人民日报》1976年3月28日发表《湖北省云梦县发掘十二座战国末年至秦的墓葬,出土一批秦代的法律、文书竹简》一文,标题即凸显了法律文献的地位。“日书”文献的书题虽首见于睡简,却未获注意,这篇报道只称之为“占卜一类的书籍”。由于法律简牍整理公布及时,资料珍贵,在国内外首先进入研究视野,并掀起了研究热潮。与法律文献的高热度不同,睡虎地秦简的早期整理本1977年线装本《睡虎地秦墓竹简》、1978年平装本《睡虎地秦墓竹简》均未含日书。“日书”名称,季勋《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一文中已征引,随后的发掘报告中也提及睡简有“《日书》等占卜一类书籍”;但日书释文、图版均未公布,日书面目不清。稍后1977年出土的阜阳汉简也有数百余片日书类文献,这批简牍的早期研究成果在介绍其中的日书类简牍时并未采用“日书”类名,只是称此类书为当时必备的工具书。当时对日书文献的性质认识不清,如阜阳《刑德》被认为是日书性质的东西,连云港花果山的几枚日历简也被归入日书。
睡简日书于1981年出版的《云梦睡虎地秦墓》中首次公诸于众,虽被定性为“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的产物”,但仍受到关注。季勋先生在介绍睡简概况时披露睡简有“日书”篇题,指出这类卜筮类书籍的存在“证明了秦不禁卜筮书。从其内容曲折反映了一些社会状况,以及从古文字研究角度来看,这一部分竹简也还有一定的价值。”1973年发掘的定县汉简也有日书简牍,1981年发表的发掘简报中讲到“在这些遗物中竹简是重要收获”,并提及经过初步整理的《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论语》《太公书》《文子》等重要古籍,未及日书。同时发表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对日书的说法是“《日书·占卜》等残简,这类残简,多数不能通读”;定县日书的这种状况,应是发掘报告中未将之列入“重要古籍”的客观原因。时至今日,定县日书仍未有整理成果公布。李学勤先生认为睡简日书早期“遇冷”的客观原因是:“两种《日书》,非常繁复,性质又是数术书,而秦汉数术久已失传,前人很少研究。”工藤元男先生奠定了日本日书研究领域的基础,他亦指出“最初刊行的文本中没有《日书》,使得学者的注意力从一开始就偏于法制史史料的方面的研究,尽管后来《日书》公开了,但对《日书》感兴趣的人依然不多”。森和先生梳理了日本《日书》的研究状况,指出“当时由于研究者的关注对象和资料公布的时差等原因,法制史研究成了秦简研究的主流,而几乎无人关心《日书》”。最初公布的日书释文无标点、句读和分段,林剑鸣先生曾感叹“《日书》之难,如读天书!”在这种艰辛研究条件下,我们仍能看到研究者对于日书文献所付出的努力与提出的卓见,并身体力行创作研究,饶宗颐、曾宪通先生1982年出版《云梦秦简日书研究》解决了《日书》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提供了从数术史角度研究《日书》的范例,堪称睡简《日书》研究乃至整个战国秦汉简帛数术文献研究的奠基之作,引发了强烈反响。吴福助先生20世纪90年代曾撰文介绍14年间睡简的研究状况,认为“日书反映秦社会生活侧面,渐受重视”;所见专题论文总计凡30余篇,成绩斐然,依研究内容大抵可分为三类:(一)《日书》中的天文、历法问题;(二)《日书》所反映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三)《日书》的命理学研究;《日书》的学术价值愈来愈被中外学者所重视。同时也指出“日书的研究目前可谓刚起步不久,因而仍有不少等待拓展的空间,值得倾力以付”。
(二)学术接触与简牍的批量出土提升了简帛日书的研究热度
借助日书释文、图版公布的推进,日书研究在日本首先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后期工藤元男先生开辟了日书研究的先河,“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曾有‘秦简研究在中国,《日书》研究在日本’之说。”1985年林剑鸣先生访日归国,举办了《日书》研读班,推出了一批有广泛影响的研究论文;由此促发了中国大陆日书研究的“热点”。1990年精装本《睡虎地秦墓竹简》出版,日书释文有了缀联、断句和注释;日书文献的使用更为便易。1986年放简日书出土,不但使睡简日书研究有了可资对比的材料,也开辟了日书研究的新领域。众多研究者涉足日书研究领域,大陆如林剑鸣、贺润坤、胡文辉、李晓东、刘信芳、吴小强、王桂钧、王维坤、杨巨中、郑刚、刘乐贤等,台湾如蒲慕州、林富士、陈守亭等,日韩如工藤元男、太田幸男、成家彻郎、森和、尹在硕等,欧美如马克、风仪诚等。研究者对于日书的认识更加成熟,对于日书研究的重要性认识更加充分。《文博》《江汉考古》等杂志专门开辟了《日书》研究专栏,《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考古学报》《文物》《江汉论坛》《考古与文物》《秦陵秦俑研究动态》《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简帛研究》《简牍学研究》《秦汉史论丛》《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秦文化论丛》《简牍学报》以及日本的《木简研究》《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史滴》等刊物,都刊发了不少有关《日书》研究的文章。20世纪末,睡简日书已渐受重视,仿佛一只丑小鸭化为美丽的天鹅,备受海内外学者青睐,日书所藴含的极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及天文历法内容,正在被不断认识和阐发。当前日书简牍已有近30批,成为简帛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日书的研究也异军突起、方兴未艾。当然日书研究兴盛态势中也有不足,如重视重点文献(睡简、放简、孔简等)而其他文献涉及不多的现象较为突出,此外,不同批次日书间相同相近内容的串联比较研究也需要重视。
(三)简帛日书语言研究与简帛日书研究相伴成长
裘锡圭先生是较早利用简帛资料进行语言文字研究的学者,裘先生1979年即利用马王堆语料中的“是是”判断句,指出“是”字判断句战国后期产生。彼时,睡简已发掘出土,《日书》语料中有与马王堆“是=”相似的语料,且数量更多;不过因材料未能及时公布,裘先生所作论述未涉及《日书》语料。裘锡圭、朱德熙二位先生1982年合作发表《七十年代出土的秦汉简册和帛书》,从简册和帛书的形制、几次重要的发现、整理工作、价值和意义四个角度立体介绍了七十年代出土简册帛书这批珍贵资料的情况,其中“价值和意义”又从“古文献学、语言学和文字学、古代社会和历史、古代思想史、古代科学技术史”五个角度展开,高度评价了简帛资料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价值,“七十年代发现的竹简和帛书的总字数估计在二十万字以上。这为我们研究古代语言和文字提供了极其重要而又丰富的资料。佚书的价值自不待言,就是那些现在有传本的古书钞本,由于与原本比较接近,作为语言资料,其价值也远远超过今本。”盖因当时《日书》材料的图版、释文尚未公布,二位先生只在古代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采用日书材料作为例证,而未对日书语料的语言学研究价值进行细说。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有关睡简语言文字研究的成果,几无利用《日书》语料者,如曾仲珊先生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语料,讨论了睡简中的数词和量词状况,未使用《日书》材料。如王美宜先生对《睡虎地秦墓竹简》的通假字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睡简有8种资料,未涉及《日书》语料。王鍈先生对睡简所见的某些语法现象进行了讨论,文章虽提及该批简牍有10种文献,但因研究所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仅含有8种文献,所以所涉及语法现象无关日书。精装标点本《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版,促进了日书研究的全面展开,日书语言的研究也有了快速发展。日本的大西克也先生利用简帛资料研究语言地域特点的成果突出,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出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论及日书语言的特殊性;国内学者如吉仕梅、石峰、魏德胜、朱湘蓉、赵岩等先生也均将日书纳入研究范围。专门或集中以《日书》为研究语料的论著也有出现。从1976年睡简日书出土,至2016年底,40年间日书文献的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初步统计国内外发表的有关日书研究的期刊论文1300余篇,专著61部,还有几十篇硕博论文和上百篇网络论文;2017年又有近50篇期刊论文和10余篇网络论文发表。
总之,简帛日书发掘出土至今已逾40年,由最初的研究语料稀少、研究力量薄弱、研究视角不丰、研究平台不足;因受益同类语料的涌现及国际学术接触的碰撞,至今已取得了长足发展。从最初的文字隶定、释文考释,到文字所记录的民俗信仰、天文历法、数术音律、语言文字等全面深入研究,研究人员日益增多,研究成果逐渐丰厚。作为简帛日书语言学研究来说,因简帛语言学是简帛学中新辟的研究方向,简帛日书语言研究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当前开展日书题材语言的专门研究,如日书语言断代研究、日书语言专书研究、日书文献疑难词语考释、日书文献常用词演变现象、日书相同相近篇章异文比较研究等值得关注。
四、简帛日书语言研究意义
(一)简帛日书语言研究对于简帛日书的本体研究有积极意义
首先,简帛日书语言研究可以证明日书语言有随时变化的特征。日书是占断吉凶的实用手册,后世称为通书,一直传承至明清,是“新发现的老知识”。对于简帛日书的时代变迁,有研究者根据其记载内容,认为不同时代日书之间的差别不大。刘乐贤先生指出日书“主要以抄本方式流传,没有定本概念,早期和晚期的内容完全有可能混杂在一块。因此,我们探讨《日书》内容的形成时代时应持谨慎态度”。晏昌贵先生指出简帛《日书》涉及的年代从战国中晚期直到东汉晚期,仔细比较简帛《日书》,可以发现其中有些基本差异乃是由于历法的不同所造成的。不过,从《日书》的书写形态和表现内容看,不同时代的《日书》彼此之间的差别其实很小。它们都是根据自然的时间节律来安排人世间的生活,关注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衣食居行、生老病死诸方面。《日书》占卜的内容,可以概括为“生老病死,衣食居行”八个字。晏昌贵先生又据放简日书既有与睡简相近和相似的地方,也有与孔简相近和相似的地方这种情况,指出这一方面固然可以帮助《日书》这一类东西是大杂烩,具有类书的性质,早期的东西和晚期的东西往往混杂在一起,《日书》的形成有一个层累的过程。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在秦统一中国前后,从西北的秦国故地到南方的楚国故地,地域性的差异其实是很小的。换言之,在秦统一前后,全国各地的区域文化可能趋于一致,民间信仰和心理认同亦渐趋一致。这是秦所以统一全国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基础。过分夸大古代中国的地域文化差异,可能并不恰当。李零先生认为日书“都是世代相传、反复使用的手册,内容完全是设计好的和程序化的,几千年来很少变化。它们并不是实际的占卜记录,更不是社会生活的写实”。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日书会有差别,但它是一种比较程序化的书,会保留一些从古到今一直会问到的问题。有语言研究者因日书杂有前代语言,而未将日书纳入断代语言研究语料。
日书的占断事项不超“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即使后世这种文献改换了名称,其占断内容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日书确实有千年不变的历时传承性。不过日书是实用文献,服务于特定时空下的不同人群,其语言必然要顺应时代变化,与时代密切接轨。赵岩先生《简帛文献词语历时演变专题研究》讨论了简帛文献的新词新义,基本范畴词语的演变、复音词的演变等内容,其中有不少论述以日书文献为主要语料,如“牢/圈/圂/厩”“覆/盖”“畜生(牲)/畜产”等范畴的演变和词义替换。我们在“简帛日书词汇应用研究”一章全面清理了简帛日书中的新词新义,当然因基于对《大词典》修正的研究目的,所以新词新义判断的主要参照是《大词典》所收词、所释义与所列书证,所清理出来的新词新义未必不见于更早期的文献。据我们统计,日书中的部分新词新义是因日书的历时异文而形成的,这尤其体现了日书语言的随时变动;当然日书语言的异时变动不独体现于词语的替换方面,在文字、语法、表达方式方面都会有所呈现;这些细致的变化,我们将在“简帛日书历时异文的语言学观察”一章进行系统介绍。
虽然日书文献所载内容被传承下来,但语言的历史变迁在不同时代的日书中都留下了印迹,新词新义和异文的产生,是日书语言随时变动的细节表现。日书文献可以作为历时语言研究的资料,起码是重要参照资料。诚如海老根量介先生所言,日书是民间俗书,而不是官文书,民间俗书是否反映当时的用词习惯还有待研究;但睡简、放简、孔简日书内容大致相同占文的字词有很细小的差异,这似乎帮助日书的抄写者及时用当时的词汇去改写,这个情况与秦汉时代的官文书极其相似,似乎可以把日书像官文书一样看作反映当时用词习惯的文献,这一点应该值得注意。
其次,简帛日书语言研究可以为探寻日书的地域归属提供支持。语言,尤其是地域特点鲜明的语言要素可以作为判断文献地域来源的重要辅助手段;如出土地不明的港简、北秦和北汉,在判断地域来源时,整理者均参考了简文所用词语的状况。出土地明确的日书文献占多数,但睡简出土于故楚地,其日书来源较为复杂,部分篇章有明显的楚系或秦系特征,多数篇章的来源尚不明确。放简日书出土之前,研究者多将睡简日书作为研究秦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等诸方面的资料,仅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睡简日书有楚系成分;放简日书出土之后,日书间有了对比,对于睡简的秦楚归属,形成了不同的意见:或将睡简日书看作楚系日书,或认为睡简日书糅合了楚秦日书的成分,或将睡简日书作为研究秦人观念的语料,或认为睡简日书无区域限制,代表了战国末年各地中下层的文化生活。睡简日书中的篇章或源于楚,或源于秦,而非均源于楚而受秦影响或均源于秦而受楚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改变了整体讨论睡简日书来源的状况,开展了分篇研究日书来源的工作。睡简日书篇章的来源推断,可以将地域明确的九店、放简作为参照,不少研究者即从此角度对睡简日书篇章的来源进行分析,如刘乐贤、森和先生等。不过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日书是资料汇抄,非足本,且九店日书数量少,不能代表楚地日书的全部,睡简中的很多篇章不能进行对比。而且这种方法的大前提意味著《日书》有着多元的起源,不同的内容起源于不同的地域,后来才汇集在一起,因此凡是性质相同的内容或篇节就应当同出一源。也有研究者据日书所反映的习俗信仰来判断睡简篇章的来源,认为除少数篇章外,多数应“代表流行于战国末年时各地中下阶层之某些文化习俗”。地域方言是文献来源的外部显性特征,尽管有学者曾指出“把《睡简》同战国时期其他文献进行比较时,没有明显发现方言的对立。过去在对傅世典籍进行语法研究时,也很少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其中的语法、词汇现象在方言上有对立。”这种现象的出现应该与“周秦时代人们在口语交际方面是使用共同语的。共同语的使用范围,大概不囿于中原地区,也延展到齐鲁和荆楚等地;使用共同语的人,不仅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而且也有普通老百姓”有关。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语言文字的使用未能完全统一;日书文献又是服务于特定时空下的具体人群的实用手册,遣词造句必然会遵循当时当地百姓的使用习惯。如果行文中渗入当地当时的方言因素或出现地表特征明显的事物名称;那么,这些地域明确的方言词和事物名称便可以作为判定日书地域来源的重要参证。
《诘》篇是睡简日甲中的一篇,“诘”是自题篇名,全篇文字书于简24背至68背共45枚竹简上,分栏书写,包括重文、文字漫漶不可识之字在内,有1900余字,是睡简日书中字数最多的篇章。《诘》篇内容完整丰富,是民俗学、社会学的重要关注语料;起初经常被用来研究秦人的鬼神信仰,放简日书公布之后,日书文献有了对比,研究者对《诘》篇的地域归属便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但目前尚未达成共识:有研究者仍将其作为研究秦地民俗信仰的材料,有研究者则据放简日书不载此类内容、楚人尚鬼或睡简出土于故楚地等因素而将其归入楚系日书。由于日书是汇抄本,累积而成;放简日书未有此类篇章、睡简日书出自故楚地,都不能构成《诘》篇楚系性质的充足条件。同时,受限于认识水平,鬼神信仰也必然有其广大且深远的影响,秦人重实际,但并非不言鬼,放简《志怪故事》即记载了丹死而复生之事并借丹之口叙述了鬼于祭祀的需求;《诘》篇虽鬼名众多,也很难构成确证其属楚系《日书》的完备条件。
地域方言是文献来源的外部显性特征。方言之间差异最大的语言要素是语音,不过受限于汉字表意性特点,用汉字研究语音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虽然如此,《诘》篇的用字现象也有楚音特点的呈现。李玉先生指出《诘》篇“梦”字作“瞢”,“贲”通“奔”(或认为通“蕡”),“瞢”通“梦”,这些语音现象具有古楚地方言的特征。语法具有稳固性,变化缓慢而细致;方言间的差异,在短期的语法层面上很难形成标志性的差异。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要素,语言的地域差别与时代变迁在词汇中表现尤为醒目;《诘》篇的方言特征也主要体现在方言词的使用上。
《诘》篇出现的楚地或相近地域的方言词有“箬、茇、 、茹、謼、丘”6个。
、茹、謼、丘”6个。
(1)人卧而鬼夜屈其头,以若(箬)便(鞭)击之,则已矣。睡甲48背叁
(2)鸟兽虫豸甚众,独入一人室,以若(箬)便(鞭)击之,则止矣。睡甲49背叁
(3)人妻妾若朋友死,其鬼归之者,以莎芾(茇)、牡棘枋,热(爇)以寺(待)之,则不来矣。睡甲65背壹—66背壹
(4)一室中卧者眯也,不可以居,是□鬼居之。睡甲24背叁
(5)一宅之中毋(无)故室人皆疫,多瞢(梦)米(㝥)死,是= 鬼貍(埋)焉,其上毋(贯)草如席处。睡甲40背壹—41背壹
鬼貍(埋)焉,其上毋(贯)草如席处。睡甲40背壹—41背壹
(6)人有思哀也弗忘,取丘下之莠,完掇其叶二七,东北乡(向)如(茹)之乃卧,则止矣。睡甲63背壹—64背壹
(7)鬼恒召人之宫,是=遽鬼毋(无)所居,罔謼其召,以白石投之,则止矣。睡甲28背叁
(8)人过于丘虚,女鼠抱子逐人,张伞以乡(向)之,则已矣。睡甲45背叁
若(箬),见例(1)、例(2);竹皮义,楚地方言。《诘》篇2例“若便”,睡简整理者读为“箬鞭”,于例(1)“若”字注:“《说文》:‘楚谓竹皮曰箬。’”箬鞭即竹皮制成的鞭子。诸家多遵从整理者训释。用竹皮做成的鞭子驱邪,可能与竹可辟邪的观念有所关联,《诘》篇提及的巫术灵物“桃枱、桃秉、牡棘、棘椎、桑丈(杖)”等均有辟邪之效。
芾(茇),见例(3);草木根义,东齐方言,《方言》卷三:“荄、杜,根也。东齐曰杜,或曰茇。”《诘》篇1例“芾”,睡简整理者读为“茇”,训为草根,认为莎茇即莎草的根。楚语色彩浓厚的《淮南子》中亦有用例,《坠形训》篇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于萍藻”;可见楚方言中亦用“茇”表示草木根义。简文中的“莎”或指莎树,“茇”为木根。
眯/米(㝥),见例(4)、例(5);梦魇义,楚地方言。《诘》篇2例,睡简整理者读“米”为“㝥”,于例(4)“米”字注曰:“㝥,梦魇,《说文》:‘寐而厌也。’字亦作眯。”诸家多遵从整理者训释。“㝥”为楚方言,表示梦魇,又写作“眯”;《淮南子·精神训》:“觉而若眯,以生而若死。”高诱注:“眯,厌也。楚人谓厌为眯。”林富士先生、刘钊先生对“眯”的梦魇义及楚方言属性有详细论证,可参看。
如(茹),见例(6);吃义,吴越方言,《方言》卷七:“茹,食也。吴越之间,凡贪饮食者谓之茹。”郭璞注:“今俗呼能麤食者为茹。”《诘》篇1例,睡简整理者读为“茹”,注曰:“茹,《方言》:‘食也。’”诸家多遵从。“茹”表吃义,属吴越方言,与楚方言地域相近。
謼,见例(1),恐惧义,江东方言。《诘》篇1例,睡简整理者读为“呼”,注曰:“謼字不清。罔呼其召,不要回答它的召唤。”王子今先生认为“以‘召’释‘謼’,则作‘罔召其召’,语义不通。《尔雅·释言》曰:‘号,謼也。’郭璞注:‘今江东皆言‘謼’。……‘謼’本身有受惊吓而畏惧之义……也许‘罔謼其召’可以理解为不要为遽鬼的召唤而恐惧。”江东言“謼”为受惊吓而畏惧,与简文文意相合,也符合《诘》篇的楚系日书属性。
丘,见例(8);坟墓义,关东方言,《方言》卷十三:“冢,自关而东谓之丘。小者谓之塿,大者谓之丘。”《诘》篇“丘”6例,简文“丘虚”非一般的“土丘”。“过丘虚”是常规行为,而非临时举止,否则不会专列“诘咎”方术。“丘虚”当为坟冢义,“过丘虚”即前往祭拜于坟冢,亦即“上冢”。古人重视拜祭祖先的行为,悬泉日书、放简《志怪故事》均有“上冢”宜忌记载。日书文献中“追”“逐”意义有别:“逐”义为驱逐,目的是驱逐走;“追”义为“追赶”,目的是追赶上。如周简日书《系行》篇占卜事项占辞均为“逐盗,追亡人”。结合“逐”在日书中表驱逐义情况,例(8)文意可以理解为:前往墓地拜祭,若被母老鼠抱子驱逐不能上前;面向母老鼠打开伞,那么它就不驱逐了。《诘》篇又有“丘鬼”,“丘”亦有单用例。
(9)人有思哀也弗忘,取丘下之莠,完掇其叶二七,东北乡(向)如(茹)之乃卧,则止矣。睡甲63背壹—64背壹
(10)人毋(无)故鬼昔(藉)其宫,是=丘鬼。取故丘之土,以为僞人犬,置蘠(墙)上,五步一人一犬,睘(环)其宫,鬼来阳(扬)灰击箕以喿(噪)之,则止。睡甲29背壹—31背壹
有研究者将“丘鬼”训为坟墓之鬼,合乎简文文意。因用于驱鬼,所以简文特意交代“莠”的生长环境为“丘下”;例(10)也因用于驱鬼,所以要求用于制作偶人、偶犬之土要取自“故丘”。
此外,《诘》篇还有1例“敲”:
(11)人毋(无)故而鬼取为胶(摎),是=哀鬼,毋(无)家,与人为徒,令人色柏(白)然毋(无)气,喜契(洁)清,不饮食。以棘椎桃秉以 (敲)其心,则不来。睡甲34背壹—36背壹
(敲)其心,则不来。睡甲34背壹—36背壹
范常喜先生认为简文“敲”表示“投”义,为楚方言,简文大意是指“用棘做成锥,并配以桃木之柄,然后向鬼的心脏部位投过去,那鬼就不来了。”鬼怪飘忽不定,行动迅速,“敲打”其心不太现实;将“敲”释为“投”于简文文意相协,其表“投”义为楚方言也合于《诘》篇为楚系《日书》的语言特点。不过《诘》篇另有8例投掷义均使用通语“投”,且“投”后虽或出现所投掷的对象、处所(如“投之道”),但未出现所投掷对象的身体部位(如“以白石投之”);唯此1例投掷义作“敲”,且其后接所投掷的具体部位,与“投”用法有别。或许此处“敲”所示投掷并非一般弃物投掷式的一次性行为,而是手持桃柄锥连续挥掷,类似于击刺,与“敲”之连续动作存在关联。不管具体意义如何,该例“敲”与通语中“敲”的语义有别,当为楚方言用法。
《诘》篇还出现了南方或常见于南方的事物名称。如“饙”,蒸米饭;大米是南方主粮,且楚地有蒸食的习俗。“䓛”,屈草;《正字通·艹部》:“䓛,《神农本经》有屈草,生汉中川泽间,主寒热阴痺。䓛当即屈。”“黄土”,黄壤;黄壤是湿润的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下形成的黄色土壤,是我国南方山区主要土壤类型之一,在滇、桂、粤、闽、湘、鄂、赣、浙、皖、台等地有相当面积,黄壤土质黏重,常分布在排水不利的平坦地段和稍低洼的积水地段。孝感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地处大别山南麓,属低山丘陵地区。具备黄壤生成的地理环境。湖北雨量和气温适中,土壤以中性的黄棕壤为主。湖南、湖北两省有以“黄土”命名的地名,如湖南常德黄土山,湖北孝感黄土岗、湖南长沙黄土岭。黄土土质黏重,加水湿润后可塑性强等特点,日书中使用黄土的方法有“洒、濆、窒”,也符合黄土土壤特质。
此外,迎接义的“逆”与“迎”,鞋子义的“屦”与“履”有历时替换关系。在战国晚期的秦地,这两组词已大致完成了替换或新词已占优势:如《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文献以“迎”为主,睡简《法律答问》《封诊式》中“履”有13例;而《诘》篇迎接义用“逆”不用“迎”,5例鞋子义均用“屦”。这种用词的不同也可帮助《诘》篇与同时期的秦系文献有别。
再次,简帛日书语言研究可以为推定日书成书年代提供线索。
睡简和放简日书是日书文献中的大宗语料,是日书研究的重要基准,关于这两批日书的成书或抄写时代,研究者有不同意见。有研究者认为睡简日书早于放简日书,也有研究者认为睡简日书晚于放简日书。
语言文字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有语言文字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因素的影响。战国秦汉时期社会变迁,政权更迭,语言文字的变动加速。《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说文·辛部》:“辠,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忧。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里耶秦牍8—461更名牍规定了56组字词(部分文字残泐)的使用情况,这些字词变更是秦统一后对语言文字干预的结果。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是判断文献写成时代的重要指标,如秦简牍中“民”与“黔首”及“辠”与“罪”的使用情况,能有效反映出部分简牍是否写成于秦统一后。
“黔首”一词在战国后期已经存在,出现“黔首”的简牍不一定就是秦统一后的文献;不过将原有文字更改为“黔首”,却应是受秦始皇“更名民曰黔首”政策影响的结果。程少轩先生即据放简2例“黔首”语句不合四言卦辞格式,不协韵脚,推断“黔首”由“民”更改而成,进而判断放简写于秦统一后。海老根量介先生据放简“民”与“黔首”,“辠”与“罪”,“殹”与“也”三组字词的使用情况,认为放简是“秦代的钞本”。关于“民”与“黔首”:海老根量介先生提供了放简改写“黔首”的其他例证,《钟律式占》(程少轩先生命名)篇章的“黔首心”是硬改熟语“民心”的结果;《建除》篇的“入黔首”是抄写者的机械更改,“黔首”似没有“奴婢”的意思,“入黔首”意思不通,睡简相应简作“人”或“人民”。关于“辠”与“罪”:海老根量介先生认为先秦出土文献“罪”未有使用,放简日书既然使用“罪”字,“其钞写年代应该在秦统一以后,而不可能早到战国时期”。关于“殹”与“也”:海老根量介先生认为放简的2例“也”仅见于《钟律式占》,《钟律式占》可判定是根据六国系统的钞本而钞写的。
《钟律式占》篇章中的“黔首”是改写“民”字的观点,应是符合实际状况的判断。我们以放简、睡简日书中“黔首、人、人民”的语句的对应情况为例,进行帮助。
放简日书中“黔首”语句,在睡简中的对应情况如下:
篇名 | 放简 | 睡简 |
建除 | 建日,良日殹。可为啬夫,可以祝祠,可以畜大生(牲),不可入黔首。放甲13(又见放乙14壹) | 建日,良日也。可以为啬夫,可以祠。利枣(早)不利莫(暮)。可以入人、始寇<冠>、乘车。有为也,吉。睡甲14正贰 |
平日,可取(娶)妻、祝祠、赐客,可以入黔首、作事,吉。放甲16壹(又见放乙16壹) | 平日,可以取(娶)妻、入人、起事。睡甲17正贰 |
直室门 | 徙门:数实数=,并黔首家。放乙18叁 | 徙门:数富数虚,必并人家;五岁更。睡甲116正叁 |
归行 | 凡黔首行远役,毋以甲子、戊辰、丙申。不死,必亡。放乙124壹 |
|
钟律式占 | 大吕,音殹。贞在大吕,阴阳溥(薄)气,翼凡三□,居引其心,牝牡相求,徐得其音,后相得殹,说(悦)于黔首心。放乙262 |
|
蕤宾,□殹,别离、上事殹,外野某殹。贞在蕤宾,是谓始新,啻(帝)尧乃韦(围)九州,以政下黔首,斩伐冥冥,杀戮申申,死不生忧心,毋(无)所从容。放乙272+280 |
|
日书《建除》篇“黔首”与“人(民)”的关系,研究已多,不再讨论。《直室门》篇,放简作“黔首家”,睡简作“人家”,“黔首”与“人”也存在异文。放简《直室门》“并黔首家”与上文“数实数=”四字格对应,为形成这种对应,前面的状语“必”被省略;放简该篇占辞肯定语气副词“必”基本都出现,如“必参寡”“必有经〖死〗焉”“必施衣常(裳)”“妇人必宜疾”“必为啬夫”“必 (癃)”,而“并黔首家”前则无。这应是“并黔首家”因“黔首”替换“民”而引发的连锁应对举措。放简《归行》篇“黔首”无比较资料。放简《钟律式占》篇章,虽亦无睡简参照;但该篇使用“黔首”的语句显然与前后语句的格式、韵律不协,“黔首”当是改写“民”字而来。
(癃)”,而“并黔首家”前则无。这应是“并黔首家”因“黔首”替换“民”而引发的连锁应对举措。放简《归行》篇“黔首”无比较资料。放简《钟律式占》篇章,虽亦无睡简参照;但该篇使用“黔首”的语句显然与前后语句的格式、韵律不协,“黔首”当是改写“民”字而来。
睡简日书中“人民”语句,在放简中的对应情况:
| 睡简 | 放简 |
建除 | 收日,可以入人民、马牛、禾粟,入室、取(娶)妻及它物。睡甲23正贰 | 收〖日〗,可以氐、马牛、畜生,尽可,及入禾粟,可以居处。放甲21贰(又见放乙22壹) |
艮日 | 离日不可以家(嫁)女、取(娶)妇及入人民、畜生,唯利以分异。49正叁—51正叁 |
|
稷辰 | 【 (秀)】,□□□车,见〖人〗,入人民、畜生,取(娶)妻、嫁女,□□□□□□□不可复(覆)室。睡乙53壹 (秀)】,□□□车,见〖人〗,入人民、畜生,取(娶)妻、嫁女,□□□□□□□不可复(覆)室。睡乙53壹 |
|
敫,有细丧,□□央(殃),利以穿井、盖屋,不可取(娶)妻、嫁女,祠,出入人民、畜生。睡乙57—58 |
|
阴,先辱后庆。利居室,入货、人民、畜生;可取(娶)妇〼葬貍(埋)、祠。正月以朔多雨,岁中,毋(无)兵。睡乙60—61 |
|
彻,大彻,利单(战)伐,不可以见人、取(娶)妻、嫁女,出入人民、畜生。睡乙62壹 |
|
睡简日书“人民”出现于《秦除》《艮山》《秦》篇中,基本是秦系日书;放简未见“人民”。
综合放简日书“黔首”语句在睡简中的对应情况,可以发现放简的“黔首”与睡简的“人”对应,放简的“氐”与睡简的“人民”对应。“氐”与“民”为形似字,以形似字替换本字是避讳的常用方法,放简使用“民”的形似字“氐”,应是避免使用“民”称呼的一种顺时替代。“更名民曰黔首”,也许是将“民”的称呼,如“人”“民”“百姓”等也一并更改为“黔首”;而非仅仅更改替换“民”字。
除2例“氐”外,放简日书有2例“民”。
(1)壬癸雨,大水,禾粟□起,民多疾。放乙158
(2)【毋射〼】,【贞】在毋射,禹以成略,溉(既)就溉(既)成,乃告民申,辠(罪)人在此,忧心贞〖=〗,身有苛(疴)疵,忧心申申,不可以告人。放乙279+311
例(1)中的“民”字迹不甚清晰,不过文献中多见“民多疾”用例,孔简日书即有4例;“民”字误释的可能性不大,“民多疾”“民疾”或为当时习语,其中的“民”不易被“黔首”替换。例(2)中的“民”出于《钟律式占》篇章,存留“民”字,语句整齐,押韵协调;即便如此,放简该篇章简文亦出现因嵌入“黔首”所致语句与同篇其他简文的行文、韵律有异,且有生造词迹象;而该篇章保留“民”的语句则行文一致、韵律相协。这种现象是放简书于“黔首”替代“民”施政政策发布之后的较好证据。
放简日书“罪”“辠”均有使用,“罪”1例,“辠”7例,以“辠”为主。海老根量介先生认为是“钞写者写‘辠’字的习惯一时改不过来,有时不小心写‘辠’字。”有研究者据放简日书“辠”远多于“罪”的情况,指出“不小心”的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显然难以成立”;放简7例“辠”,4例“民”是这批简属于秦统一之前的有力证据。“黔首”与“民”的差异度远远大于“罪”与“辠”:“黔首”与“民”属于词语的更换替代,且“民”改称政令推行前“黔首”一词民间已有使用,“民”更改为“黔首”的操作性更强,即使所抄写的底本未作“黔首”,抄写者也易发觉,并做出有意改动;“罪”与“辠”仅是形体相近的文字变更书写形式,且“辠”构形理据清晰,抄写者对“辠”更改为“罪”的敏感度受限,易受汉字形体表意的潜在影响而“因意”书写或未尽更改。从这个角度看,改“罪”为“辠”难度大,易疏漏。
放简日书语气词“殹”“也”均有使用,以“殹”为主,“也”仅2例。“殹”为秦方言字词,“也”为通语字词,秦文献惯于作“殹”,但未限用“也”;放简日书中的“也”未必受到六国影响,可能是承袭了通语字词用法。
也有研究者从其他角度立论,指出放简日书晚于睡简日书。如姜守诚先生以放简日书“除”有“除罪”义,而睡简日书“除日”并不具有“除旧布新”功能,认为这种区别当是建除说在流传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次理论创新。晏昌贵先生则据睡简、放简、孔简占盗简文是否附有盗者名字,推断放简似乎是位于睡简与孔家简之间的中间环节。
总之,放简出现有意改“民”为“黔首”的用例,应是顺应秦始皇书同文政策的结果;同时,与睡简相对应的简文出现了新的词义或改为更科学的表述方式。放简日书的抄写时代应略晚于睡简,当在秦统一颁布语言文字规范政策后。不过,日书具有汇编性质,放简日书中某些具体篇章的形成时代未必晚于睡简。加之,语言文字现象复杂,日书又是民间文献,其语言文字的更改未必如官方文书一样严格。如里耶秦简8—461更名牍有“曰产曰疾”,牲畜义要说“产”;但放简《建除》篇依然使用“生”:放简日甲简13建日有“大生(牲)”,简15盈日有“生(牲)”,简21收日有“畜生”,其中“生”单用1例;惜放乙篇《建除》不存“盈日”条,不能完全确定《建除》篇“生”“产”是否存有替换现象。但就日甲《建除》篇保留了畜生义的“生”而言,或能帮助该篇未执行秦始皇书同文政策,其形成年代较早;但是《建除》篇用“黔首”而不用“人”,“黔首”或是顺应书同文政策的改写(放简《建除》篇“氐”与睡简《秦除》篇“人民”对应,也帮助放简书者注意到了“民”的变动规定)。所以,不能完全排除放简《建除》篇“生”的存在与放简“罪”“辠”共现一样,有未能及时替换的原因。
又次,简帛日书语言研究,可以为了解日书的流行层次提供辅助资料。
研究者一般认为日书是服务于普通百姓的趋吉避凶的实用手册,代表了社会中下阶层的文化心理。也有研究者提出日书的“使用对象不是一般百姓,而是相关官吏”“《日书》直接反映了官吏们的希求和禁忌”。
日书滋生、盛行的时代,阶级分明,某些词语包括某些常用词语有特定的适用阶层。如“死亡”语义场包含了因对象不同而产生的多个成员,《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日书“死亡”义位同义词未有阶级分化的功能,如“奠、击、尽、老、丧、死、亡、畏、殚亡、丧生、死丧、死亡”等,其中“死”使用频率最高。再如“妻子”语义场包含了因丈夫社会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多个成员,《礼记·曲礼下》:“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日书“妻子”义位同义词有“妇”“妻”两个,两者存有异文,均指平民之妻。从“死亡”“妻子”同义词成员来看,日书服务的对象是社会中最大群体即普通百姓,日书汇集的目的也是为了给普通百姓提供趋吉避凶的实用手册。
基层官吏墓葬中葬有日书,一是因为日书中有适用于官吏行事宜忌的占辞,这些占辞应是普通民众希望子孙甚至自己能为官为吏,生活富足,并为此配备占辞,基层官吏可以利用日书中的相关占辞指导自己的施政行为;二是基层官吏借助日书了解熟悉民众的风俗信仰,生活宜忌,方便治理治下百姓;三是基层官吏也是社会中的个体,其日常行为受社会普遍认同的生活宜忌制约。
(二)简帛日书语言研究对汉语断代、汉语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简帛日书文献具有出土文献的共性优势。出土文献文本真实,时代确定,地域明确,是显见事实,并多被研究者反复提及,且得到学界公认。当然日书文献也有确切时代存在争议者,如放简日书,但其上下限时间跨度小,不同于某些传世文献的时间不确定。日书文献也有地域来源不甚明确者,如收购、入藏的日书,不过这些日书的地域来源也可以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内容,竹简的物理属性等多种参照进行大致的推断。睡简日书来源复杂,这种杂糅秦楚两地日书的简牍,在日书简牍中也并不多见;且部分篇章有明确来源标志,有的篇章可以据语言特点、语言所反映的现象来推断地域来源;来源不明确的篇章只影响地域层面的习俗、信仰、语言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于断代层面的社会、数术、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都是很好的值得利用的资料。就语言学研究而言,“专书研究是断代研究的基础,而断代研究又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因此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开展各代的专书研究,全面考察、描写其中的语言现象”。“如果大家的兴趣都集中在某一个时期的某几部书上,而另一些时期的专书却无人研究,那么史的线索还是贯穿不起来。”简帛文献语言学虽起步晚于甲骨文、金文,乃至石刻、敦煌文献的语言研究,20世纪末才渐有研究专著问世,如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1994),张显成《简帛药名研究》(1997);不过简帛语言研究发展迅速,近年来已有不少专著,如魏德胜《〈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研究》(2000),魏德胜《〈睡虎地秦墓竹简〉词汇研究》(2003),吉仕梅《秦汉简帛语言研究》(2004),周守晋《出土战国文献语法研究》(2005),王颖《包山楚简词汇研究》(2008),李明晓《战国楚简语法研究》(2010),李明晓等《战国秦汉简牍虚词研究》(2011),张国艳《居延汉简虚词通释》(2012),张玉金《出土战国文献虚词研究》(2012),朱湘蓉《秦简词汇初探》(2012),赵岩《简帛文献词语历时演变专题研究》(2013)等;简帛文献语言研究的硕博论文、期刊论文的数量更多。简帛语言学的迅速发展,从一个侧面帮助简帛语料之于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这些简帛文献保留书写时的原貌,是珍贵而真实的“同时资料”,是语言学传统研究语料的重要补充。而简帛语言学的专书、断代研究,也为汉语词汇、语法、语音的横向共时以及纵向历时研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时代坐标。
简帛日书文献有作为题材语言的鲜明特点。第一,简帛日书语言易于随时异动。日书文献具有实用性,时刻要参与对当下之时、事的占断,要反映新事物、新现象,这就要求或使得其用时语表述占断事项与占断结果,语言也因此更易与时俱进,随时异动。所以,日书文献所呈现出的是保留着当时语言面貌的活语言,未有如经典文献所经历的编者加工修正补充程序。第二,简帛日书语言接近民间口语。日书主要服务于社会中下层成员日常生活、生产事项的占断,在民间流行,语言通俗,口语性强。《史记·龟策列传》张守节正义:“日者、龟策言辞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即点明《史记》中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言辞鄙陋,非太史公本意,而由其本身言语鄙陋所致;而“越是口语性强的文献,就越有语言研究价值”。日书语言的口语性有多方面的表现,如日书中对选时择事有诸多禁忌规定,同时也述及不合宜忌规定的时、事的结果与后果,其中必然使用大量的假设复句;但是日书中的假设复句使用假设连词的频率很低,假设连词仅出现“女(如)”“若”“节(即)”等少数几个。日书中的假设复句基本靠语义直接串联,如孔简275贰:“寡门:不寡,日泥兴,兴毋(无)所定处;弗更,必再寡,凶。”简文的意思是:投掷于寡门,如果不寡,而终日执着于兴盛,即使兴盛也没有固定居所。(需要变更居所),如果不变更,一定会再次守寡,不吉。简文两处假设,均未使用假设连词。第三,简帛日书非一人所作。日书来源复杂,非一人之著作,关于这一点,研究者已多有论述;因为它源于众人,能避免语言运用方面的个人色彩,因而具有更广泛的社会通用性。第四,简帛日书内容丰富。出土文献有诸多优点,是语言研究不能忽视的重要语料,不过也有研究者提出诸如甲骨文、金文、公文简牍等文献有语言研究方面的局限性,如语言程序化、残断过甚、内容不丰等。日书虽占断形式程序化,但占断内容丰富,涵盖面广,覆盖生活、生产的诸层面,“是一部人们一切生活起居行动中如何趋吉避凶的百科全书”;且有长篇,而依凭研究经验的积累和科技手段的进步,残断竹简的缀联更易于操作。第五,简帛日书数量丰富。有研究者统计过秦代出土的简牍,其中占卜类书目所占比例高达35.7%。简帛日书已发现有近30种,随着日书资料的整理及再出土的可能,大量日书文献无疑为包括语言学研究在内的诸多研究提供了一座宝库。简帛日书的这些特点,具备了汪维辉先生所讲的有价值语料的条件:“反映口语的程度”“文本的可靠性”“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度”“文本具有一定的篇幅”,“一般来说,上述四个方面的正面值越高,语料的价值就越大。”
此外,简帛日书既集中于上古汉语时段,又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从战国晚期早段开始一直到西汉晚期,甚至也有东汉时期的日书文献出土,而大宗材料又集中于战国秦西汉,这使得它可以作为上古断代汉语研究的语料。同时,相同篇章的内容在战国秦汉不同时期的日书中重复出现,这些相同篇章语言的细微变化,又是体现大时段内语言局部微变、量变的珍贵语料。简帛日书虽与后世通书性质相同,但近代以前这类文献未有传世文献,简帛日书不同于传统的上古汉语的研究语料,李零先生指出“过去研究简帛,大家是把档案和典籍放在一起研究,学界只有笼统的‘简牍研究’或‘简帛研究’。现在,由于材料山积,已经到了不得不分开的地步。”简牍分题材研究,如典籍语言研究(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简等)、公文语言研究(居延汉简等)、军事语言研究(银雀山汉简等)、医学语言研究(马王堆汉墓帛书医简、武威医简等)、法律语言研究(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等领域已取得不少成果。沈颂金先生曾指出“过去我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精英阶层文化,即《汉书·艺文志》中前三类——六艺、诸子、诗赋,而忽略后三类——兵书、术数、方技。出土的简牍、帛书文献却有相当大的部分恰恰是‘兵书’、‘术数’、‘方技’,天象星占、择日龟卜、医方养生、兵家阴阳的知识在古代随葬文献中的数量,表明它在实际生活中占了很大的分量,也常常是古代思想的背景”。简帛语言研究新世纪以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简帛日书的语言研究应该讲还未全面系统开展起来。简帛日书的多批次出土,使得这种专业特点鲜明的文献在文字考释、词语解读等方面有了较为充分的可借鉴的成果,简帛日书语言研究已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先导性研究积累。日书文献是汉语断代和汉语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语料,其中日书词汇研究可以补充《大词典》因时代局限未收的日书词目和书证;这可以看作是最直接、最实用的研究意义了。“新的发现带来新的学问”,当前阶段的语言研究需要留意该类型语料中的语言现象,进行有意义的系统研究。总之,简帛日书的语言研究已提上日程,并具备了研究的可能性。
(三)简帛日书语言研究可为其他学科的深入研究提供支持
李学勤先生指出:“对于日书,至少可从两方面去研究:一方面,是从数术史的角度考察。……另一方面,对《日书》的内容还可以作社会史的考察。”当前日书资料运用最成熟的是社会史研究领域。而文字的正确隶定、词语的准确解读、篇章的合理编排,是运用日书文献进行社会史、数术史等层面研究的前提。如果对语言文字理解有误,则有可能得出不合实际的结论。如:
(1)取(娶)妻,妻不到。以生子,毋(无)它同生。睡甲78正壹
有研究者认为上例简文中的“以”通“已”,修饰其后的“生子”,简文反映了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先孕的现象。
上述简文出自《星》篇,我们将简文录全,辅以同篇其他简来理解简文文意。
(2)须女,祠、贾市、取(娶)妻,吉。生子,三月死;不死,毋(无)晨(辰)。睡甲77正壹虚,百事凶。以结者,易择(释)。亡者,不得。取(娶)妻,妻不到。以生子,毋(无)它同生。睡甲78正壹危,百事凶。生子,老为人治也,有(又)数诣风雨。睡甲79正壹
睡简日乙《官》篇、孔简《星官》篇有与上述文字相应的简文。
(3)十二月:婺女,祠、贾市、取(娶)妻,吉。生子,三月死,毋(无)晨(辰)。睡乙105壹虚,百事〖凶(凶)〗。以结者,易择(释)。亡者,不得。取(娶)妻,妻不到。以生子,毋(无)它同生。睡乙106壹【危】,百事凶(凶)。生子,老为人治也,数诣风雨。睡乙107壹
(4)十二月:婺女,利祠祀、贾市,皆吉。以生〼毋(无)辰。司命。以亡者,不盈五岁死。不可取(娶)妻、嫁女。虽它大吉,勿用。孔58虚,百事凶。以结者,易□□□□□。取(娶)妻,妻不到。司死。以生,毋(无)它同生。不可取(娶)妻、嫁女。虽它大吉,勿用。孔59【危】〼□□□数诣风雨,大凶。孔60
《星》《官》《星官》篇采用星宿记日,须女(婺女)、虚、危三个星宿值日的占辞均涉及生子事项。孔简中虚宿值日占辞“取(娶)妻,妻不到”与“以生”之间有“司死”隔开;可知,“取(娶)妻”与“生子”是两个不同的事项,“妻不到”与“以生子”前后之间没有因果逻辑关系。睡简《星》篇虚宿所值日简文的意思是:虚宿所值日,百事凶险。这一天结盟的,容易放弃。逃亡的,不能抓到。娶妻,妻子不来。生孩子,没有其他兄弟姐妹。
通过完整占辞可以看出例(1)中“以”为介词,其宾语即“虚”所值时间;只是“虚”所值日涉及多个事项,为叙述简单,各事项前通用一个前置“虚”来表示。
再如:
(5)丁酉生子,耆(嗜)酒。睡甲143正叁
有研究者认为此例是秦饮食礼俗的记载,反映了“生孩子也都要喝酒庆祝”的礼俗。
该简出自《生子》篇,全篇为不同时日生子命运的占辞。列举几条如下:
(6)丙午生子,耆(嗜)酉(酒)而疾,后富。睡甲142正肆
(7)戊午生子,耆(嗜)酉(酒)及田邋(猎)。睡甲144正伍
对比例(6)、例(7),例(5)中的“耆酒”不当理解为“喝酒庆祝”。“耆酒”“耆酉”即嗜好喝酒之义,“耆(嗜)”与“好”表义相同。
(8)壬辰生子,武而好衣剑。睡甲148正贰
(9)戊戌生子,好田壄(野)邑屋。睡甲144正叁
本研究内容包括简帛日书数术术语汇释、简帛日书同义词研究、简帛日书历时异文研究、简帛日书词汇应用研究,以期在梳理出日书文献特色词汇数术术语的基础上,开展简牍语言一般现象研究,通过共时同义词梳理、历时异文分析,讨论日书语言的共时词汇特点与历时语言发展,并通过日书词汇整理为正在进行中的《大词典》修正工作提供资料。诚如研究者所言,日书是一个很粗糙的东西,问的都是老一套,问的大事也不多,对研究历史作用不大;我们在研究语言现象时,也尽量避免藉由日书中可能存在讹误的个例或不规范用法去讨论与经典文献相背的语言规律。
近年来日书文献出土颇多,我虽用心研读,但懵懂于数术原理与数术推演,必有语言阐释之失误;近年来日书文献及相关研究论著极丰,我虽尽力收集,但个人能力不达,必有未得寓目之成果和未能领会之观点。诚恳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正,以补我的不足。
编辑:赵露晴 初审:刘雯 复审:俞林波 终审:张兵